马少波:周总理始终把民族艺术放在重要位置
1918年3月生,山东莱州市人。1937年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司令部秘书长、胶东文化协会会长。1949年调京任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秘书长,文化部党组成员,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中国京剧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中国艺术语言研究会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文化部振兴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戏曲学院名誉教授,《中国京剧史》及《中国京剧百科全书》编委会主任等。2009年10 月,中国戏剧家协会授予其终身成就奖。2009年11月29日在京病逝。
-在前线为邓小平、刘伯承等淮海战役的领导同志演出过两个晚上
我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第二年就参加了八路军,担任了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司令部的秘书长,1943年调到文化系统。我在胶东文协负责时,延安开始戏曲改革,排演了《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等戏。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我也从事戏曲改革的工作,整理了很多优秀的传统剧目;我自己也创作了《闯王进京》、《木兰从军》、《关羽之死》等剧。现在看来,当年全国解放区的代表剧目主要有三个:《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和《闯王进京》。这是从中央到文艺界这样认定的,现在出版的《大百科全书》以及《解放区文学大系》,都体现了这样的看法。所不同的是,《逼上梁山》是在延安创作的,毛泽东看过,并写信给了很高的评价,而我的《闯王进京》当年毛没有看到。
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了。山东人民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支援大军,奔赴淮海前线。文艺界当然不能落后,11月,成立山东人民淮海前线慰问团,由10个文艺团体组成。我所领导的胶东文协胜利剧团是其中之一。这个慰问团总团长是郭子化,我是副总团长。到了淮海前线后,各个剧团分散到各个战场上去,而胶东文协胜利剧团是个京剧剧团,分散了就无法演出,所以仍然保持完整的演出队伍,由我带领,在前线进行演出。
在前线,这个剧团为邓小平、刘伯承等淮海战役的领导同志演出过两个晚上。头一天晚上的演出内容,是一些折子戏,第二天晚上,演出了我创作的《关羽之死》,刘、邓等领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49年1月,徐州解放了,淮海战役也结束了。总前委在徐州召开了淮海战役祝捷大会,党政军领导同志都参加了。我们团演出了我创作的《木兰从军》。
慰问团回到山东。我调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工作,负责筹备山东省文联。5月,我接到了中央发来的通知,7月1日在北平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要求6月份报到。山东分局的代表参加了华东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是6月23日成立的。团长是著名剧作家阿英,我是副团长。我从济南上火车才发现,我们与南方代表团(也即国统区代表团)竟然同车。上海电影戏剧界的袁雪芬、白杨、周信芳、梅兰芳、熊佛西、张瑞芳等,都在车上。
-周恩来拍了一下桌子说:“今天就是要让少波同志讲嘛!你们让他讲嘛!”
6月26日,我接到通知,周恩来副主席要约见解放区从事旧剧改革的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汇报工作,交流经验。我来到了中南海的西花厅。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会议的除周扬、阳翰笙、田汉等同志外,还有几个大区的代表:华东区的有阿英、陆万美和我,中南区有崔嵬,陕甘宁边区有柯仲平、马健翎,东北的是刘芝明。
周恩来同志作了简短的开场白后,突然指定由我先发言。那一年我31岁,是参加会议人中年龄最小的,在座的有好多人是我的师辈。这样一个各路诸侯的会议,恩来同志为什么指定我先发言?事前没有人给我讲过,事后我也没有问过别人。但是,我估计,大约是周扬事先向恩来同志讲了我个人在戏曲创作方面的情况,以及胶东文协进行戏曲改革方面的成绩吧?
当时,我虽然有些紧张,但还是按照事先的准备,根据自己数年来的工作经验,分三个部分谈了谈自己的想法。第一部分,我谈了谈中国戏曲的美学价值;第二部分,我汇报了胶东戏曲改革的简单情况和主要经验;第三部分,我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希望恩来同志和周扬同志在即将召开的文代会的报告中,设专章来谈旧文艺、旧戏曲改革的问题,阐述一下新中国成立后对旧戏曲的改造的政策;二是希望中央能成立全国性的戏曲改革的领导机构和研究、试验机构,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戏曲改革运动。我之所以提这样的建议,是因为在从事戏曲改革的过程中,有这样的体会:中国的戏曲源远流长,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些优秀的剧种已经灭绝,有的也濒于灭绝了。如果再不抢救,戏曲就面临着衰落的局面。我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靠政权来扶持,依靠党来领导。否则的话,戏曲就要完了。在发言中,我把这种体会,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
在我的发言过程中,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小插曲。当时,我与刘芝明坐在一起,在发言约有10分钟左右,芝明同志扯了扯我的衣襟,低声对我说:“少波同志能不能说得扼要一点,留点时间让大家都说说。”我还未来得及说话,坐在对面的恩来同志听到了,他拍了一下桌子说:“今天就是要让少波同志讲嘛!你们让他讲嘛!”这样,大家都肃然了。在这之后,我与恩来同志见过多次,但在我印象中,还从未见过他这么严肃过。
于是我又接着讲。我讲得虽然简略了一些,但主要的意见还是谈出来了。我讲完后,大家一致鼓掌。接下来发言的同志,对我提出的建议,也都表示了赞成的意见。当时,我确实感到很高兴。
周恩来最后作了总结。他讲了戏曲改革的重要意义,肯定了既有的成绩,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对于我所提出的两个建议,恩来同志也专门说到了。他说:“在我的报告里面设专章来谈戏曲改革,我可以接受;关于成立全国性戏曲领导和研究机构的问题,我个人是赞成的,但须请示主席,然后由中央决定。”
29日,周扬通知我,让我马上到他那里去。我去后看到了田汉。周扬说,总理来电话,等一会儿要来车接我们去见主席。当时,我的心情虽然很激动,但不知要谈什么。周扬没说,我也不好问。
总理和我们一起去见主席的。总理向主席介绍后,我才知道,还是谈戏曲改革的事。主席要听听我们的意见。因为建议是我在26日的会上提出来的,所以,这次还是由我先说。我把上次会上第三部分的发言简略地说了一下。主席听得很认真,没说赞成也不表示反对,只是不住地点头。我说完了以后,大家又议论了一下,主席才说:“这个问题等最后中央来定吧。”
7月2日到19日,第一次文代会在京召开。7月6日,周恩来同志作政治报告。报告里的第二部分“文艺方面的几个问题”中,着重谈到了改造旧文艺的问题。代表们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我自然心情更为激动。恩来同志的讲话,宣告了中国戏曲的改革前景,后来数十年的实践证实,这是对旧文艺“推陈出新”方针在新形势下的理论准备和指导纲领。
我感到更高兴的是,7月18日,周恩来便正式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戏曲改革领导机构的决定。随后,在周扬的具体领导下,宣布成立中华戏曲改革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欧阳予倩为主任,田汉、马彦祥、杨绍萱任副主任,我担任了秘书长。7月27日,开始在南河沿夹道小红楼正式办公。10月2日,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成立。不久,在这个委员会下又成立了京剧研究院(梅兰芳先生担任院长)、戏曲试验学校(田汉兼校长)、大众剧场(马彦祥兼经理)以及新戏曲书店(我兼经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戏曲书籍出版机构)。
-周恩来回京后的第一天上午就打电话给我,问《白毛女》什么时候演出?
1951年4月,鉴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成绩,以及为适应下一步戏改工作的进行,经周恩来批准,戏曲改进局撤销,在原有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戏曲研究院,由梅兰芳担任院长,我和程砚秋、罗合如任副院长,归文化部领导。毛泽东为建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直接主持这一重大举措的周恩来也欣然命笔:“重视与改造,团结与教育,二者均不可缺一。”这就成为全国戏曲改革工作的指导方针。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全国的戏曲改革工作蓬勃发展,欣欣向荣。1952年10月6日至11 月14日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的。参加会演的有23个剧种,1600余人,演出的优秀传统剧目、新编历史剧、现代戏共82个剧目。周恩来对这次会演很重视,他抽出时间观看了一些剧目,并与演员进行交流。期间,他接见了全体演职员并做了重要的讲话。
周恩来对戏曲的贡献,还可以从他对中国京剧院的关心上可以看出。1955年,在中国京剧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京剧院,由梅兰芳任院长,我任党总支书记、副院长。那时,周恩来总理对京剧非常重视,对京剧院的工作直接过问。
在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是,总理对京剧《白毛女》的关心。1958年,我们剧院准备将歌剧《白毛女》搬到京剧舞台。我们把这一想法报告了周恩来,他热情地表示支持,并给我们作了指示。4月初,戏排出来了,总理当时在缅甸访问,未及观看,但他对此是十分关心的。他回京后的第一天上午,就打电话给我,问《白毛女》什么时候演出?我回答说:今天是星期日,下午人民剧场正好有日场。他知道后,下午就赶来看戏。因他晚上还有外事活动,他看完戏以后未及与我们谈意见就离开了。
当天深夜,我和阿甲接到了总理的电话,要我们马上到西花厅去。见到总理后,他详细地谈了对这出戏的意见,既肯定了成绩,又对表演艺术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谈话一直持续到凌晨3时。在回家的路上,我心潮起伏,总理日理万机,但他把民族艺术始终放在重要的位置。
-我挨整时,周总理依然关心我
中国京剧院在归属上是文化部,但是因为周总理直接关心,我们做工作计划时,往往在报文化部的同时,还直接报送周总理。我不太懂得处理这些关系,大概引起了一些同志的不满意。1961年,周扬领导调整文艺政策,中国京剧院却开始了对我的批判。那时,中宣部、文化部和北京市委组成了工作组,进驻京剧院,我靠边站了,工作组与京剧院的某些同志背靠背揭发批判我。
批我的人知道我与总理的关系密切,怕我“通天”,所以想办法割断了这个关系。到了1962年,总理招待关肃霜等人时,见我没有参加,就说:“马少波怎么没来,去请他来。”去接我的人没有找我,却把马彦祥接到了总理那儿,并给总理说接错了。其实,这是文化部的个别领导故意这样做的。但这说明,总理对我还是十分关心的。
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很大,对京剧院的工作也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直到现在想起来,我还是感到痛心。京剧院成立后,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但这次整风,却人为地中断了一些工作。几年以后,江青插手,京剧院的黄金时期也就过去了。当然,“文革”期间,江青插手京剧的同时,我们这些人也遭了殃,江青点了我的名,并进行了迫害。
-在诗中用“襟怀磊落兼人勇”来表达我对周扬的敬重之情
还值得说说的是,我和周扬同志的交往情况。
我和周扬是在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期间认识的。其后,周扬让我作为他的助手,负责筹备文化部。文化部成立后,周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我作为党组成员之一,兼任戏曲改进局党总支书记。1951年4月,戏曲改进局撤销,在原有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戏曲研究院,由梅兰芳担任院长,我和程砚秋、罗合如任副院长,归文化部领导。周扬对我非常友好,我从他身上受益很多。那时,我写的文章都要先送他审阅,他都认真地做些改动。
1953年,文化部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作为党委委员的我,参加了整个大会。周扬作了报告。会议的最后一天,我就周扬的报告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我在发言中,首先肯定了周扬领导文化部党委的成绩,并拥护这个报告。然后我说,要给周扬同志提点意见。我的意见是:周扬同志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尽管有时候有点自我批评,但也是用插科打诨的方式,表现得不够严肃。那时,周扬的权威很大,位高气盛;而我呢,是年少气盛,说话直率。虽然我的发言也没有什么错误,或者是违反组织原则,但在那样的场合下,确实让周扬有点下不来台。周扬虽然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但他显然不高兴了。从此以后,我就感觉到,我和他的关系有些疏远了,来往也少了。
由于京剧院与总理的关系很密切,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文化部某些领导同志不满,他们认为马少波不理文化部,直接通天。虽然我不知道周扬的看法,但部里某些领导的这种看法,肯定对他是有所影响的;或者,换句话说,他是知道某些领导的看法的,他的不表态,事实上也就默许了某些领导对我的意见。到了1961年我挨批时,周扬对这事是知道的,也是支持的。
“文革”结束后,周扬又回到文艺界,后来担任中宣部副部长。1979年底,在万寿路的中组部招待所,周扬主持召开了中国剧协常务理事扩大会,我也参加了。周扬作了四十多分钟的报告,有两处提到我。一处说,少波同志是戏曲改革的开创者,从解放区到建国之前,在戏曲改革方面做了很多的开创性工作,成绩卓著;建国后也作出了很多贡献。另一处说,少波同志写了很多的剧本,希望以后再多写一些。
会议结束后,我回家跟老伴说了这个情况,并分析说:“看来,周扬同志对我的态度有所改变了。”老伴说:“咱们去看看他吧。”
大年初二,我和老伴就去看他。我们并没有与他电话预约,到了那里,才让传达室的同志通报。周扬知道后,亲自到门口来迎接,非常热情。
在沙发落座后,周扬说:“你过去是胶东文化界的头头,你有一定的写作能力,也有一定的组织工作能力,总理对你的评价是很高的。1961年的事情,由于我的官僚主义,不了解情况,我支持了他们,没有支持你。这件事我至今引为憾事。我过去错认了两个人,现在我又错认了两个人。”
周扬说到这儿,我就把话拦住了。我说:“1961年的事情,我对周扬同志是有意见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周扬同志你不必再说下去了,今天有你这样几句话,我也就释然了。关于我个人的遭遇、得失,微不足道,令人痛心的是,由于领导上的失误,几乎毁掉了一个中国京剧院。周扬同志,你会理解的,中国京剧院在全国的京剧事业中是个什么样的位置。”
周扬同志点头同意:“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把话题就扯开了,聊点闲话了。
这次见面后,我们的关系又密切起来,可以说比解放初期更亲密,更友好。我时常到他们那里去,我的戏,像《西厢记》等等,演出时他都来看,看后都给予很高的评价。有一次,他看完戏后,对我老伴说:“少波的戏很好,很好。”
我喜欢书法,有时候也写点字。周扬是知道的。1985年,他住进了医院,身体很不好,说话已经不是很利索了。有一次,我到医院去看他,闲聊时,他对我说:“少波同志,你书法好,给我写幅字吧。”
周扬有此要求,我当然愿意照办。回到家后,我提笔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承周扬同志面索墨迹书奉咏怀
莫道是非无宝镜,风霜过后有新晴。
襟怀磊落兼人勇,一笑胸间玉宇澄。
1985年4月
我裱好送给周扬同志后,他非常高兴,把它挂在了客厅的南墙上。他去世后,我到他家吊唁时,这幅字依然挂在客厅里。可见,他是喜欢这幅字的。
我提笔写这样的诗,是我与他半个多世纪交往的感受。上面说到,1953年我在发言中认为周扬同志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并引起了他的不满。但在“文革”后,他经过10年的监狱生涯,对我们党的历史和文化工作进行了反省,现在人们都说是反思。此后,他的胸怀相当宽阔,以别人所不可能有的勇气,对历次运动受到伤害的同志赔礼道歉。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是,在萧军八十寿辰的祝贺会上,周扬同志作了发言,他说:认识一个人很不容易,以前,我做了些错事,今天,我给大家道歉。当时在座的有萧军、胡风、丁玲等人,大家都对周扬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论语》中有一句名言:“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韩愈说:“ 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人能知自己的过处,是大智,坚决改之,是大勇了。从这意义上讲周扬是做到了大彻大悟,大智大勇。所以,我恢复对周扬的尊重,我敬重他这种磊落坦荡的人格。所以,我在诗中用“襟怀磊落兼人勇”来表达我的敬重之情。
周扬住院,与1983年他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会上所作的报告有很大关系。他在报告中谈到了“人道主义”,谈到了“异化”,他的文章我也没有仔细读过,而且我对这个问题也没有研究;胡乔木的文章,老实说,我看不懂。在这个事件中,且抛开是非不论,我认为,某些同志对周扬是过于苛刻了。周扬熬过了10年监狱生涯,得以生还,为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对党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即使他的报告中有错误,也不必这样对待他。对周扬这样的老同志,是不是有点太冷酷了。这样的做法,对周扬的打击也很大。对此,我感到非常痛心。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我在诗中写下了“一笑胸间玉宇澄”的句子,当然是表达我的心情,并劝他对此看开些。
◎口述/马少波 整理/徐庆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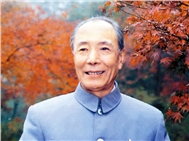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