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耀华或为中国最早得知日军侵华者之一
1936年,资耀华第三次赴日考察,嗅出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气息。“过去日本老百姓看到军人士兵,非常爱戴,非常亲热,这次老百姓看到军人,好似非常畏惧,总是敬而远之。过去军人不常上街走动,也不带武器,这次则是全副武装、高视阔步。真有点箭上弦、刀出鞘之感。” 尤其是老同学室伏高信看到他大惊,将其拉到一处偏僻的小饭馆推心置腹的一番话,让资公如梦初醒:“您怎么这个时候还来日本?日本军阀已准备大举侵略中国,这不是今年、明年的事,而是今天或明天的事了。您得赶快回中国去,否则就可能当俘虏了。”
回津后,资耀华立刻走访了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两位经理,以及南开大学两位经济学家何廉及方显廷博士,将听到的秘密消息告知他们。两位学者一致认为:“金融业将来可能被日寇拉拢利用作为其侵略中国的工具。”
除此四人外,资耀华没再对任何人透露这个秘密,甚至包括自己的家人。他担心引起不必要的慌乱,也怕传到日本特务的耳中,不仅会招来性命之忧,也会连累室伏高信。 在天津分行,资耀华开始暗中收缩放贷,并收回租界之外的贷款,重点转向租界之内的业务。既不能明说,又不能不做,委实颇费踌躇。他当时以为有租界作庇护,可以苟且偷安,事后感慨道:“这种想法,不但是太天真,而且是懦夫意志、一厢情愿。” 从此资耀华每天总是过着神经紧张、忧心忡忡的生活,自言如一叶小舟航行在大海大洋中,恐惧地等待十级大风暴的到来。 果如两位老教授所言,华北沦陷后,天津租界内的金融市场上就出现了老法币与日伪联银券的生死斗争。日本对中国经济、金融的掠夺,正是它“以战养战”的重要内容。
而资耀华此时接到的总行电报指示是:“坚守岗位、保存资产、利用租界、抵抗敌人。”而且联络团结全体同业共同对敌的“兴亡之任”,也落到了资耀华的肩上。 此时的资耀华颇为为难,他不能明说自己有指示,又不能指手画脚引起同业不满。于是苦思冥想出了一个“银行家午餐会”。 他找到天津市银行公会的秘书长郑诵先,此君多才多艺、长袖善舞,更兼对饮撰烹饪大有研究,颇能做出几道名菜,还煮得一手好咖啡。午餐会每天座无虚席。资公最大限度地利用茶余饭后之机,用自己的语言传达秘密消息以及指示,大家一起讨论出主意,指示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求天津市全体同业,无论遇到敌人如何威胁利诱,决不可与其合作,不能当面直接拒绝,则设法推辞拖延,更要与租界英美法外国银行联系,一致维持法币信用。
这种在金融市场上银行界同仁一致抛弃伪联银券的“货币战争”,使社会上的法币逐渐隐藏起来,而伪联银券却泛滥成灾,令日伪痛恨却有苦难言。 但也因为此,日军更把租界当作眼中钉,必除之而后快。于是在入侵租界到日本投降这四年,资耀华经历了人生中最痛苦的岁月。1944年更发生了一桩惊险之事,伪华北政府经济总署突然给天津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发出聘书,要成立伪华北经济委员会,用来控制华北物力、财力,接济军用。资耀华也收到了委任书。他视作奇耻大辱,当即将委任书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同时嘱咐家中准备棉衣棉裤,等待宪兵队捕捉入狱。最终不知何因,居然躲过一劫。但他忧心成疾,直到抗战胜利后去美国才得到完全根治。
在天津沦陷的日子里,资耀华天天躲在被窝里听重庆的广播,对当时的中央政府是寄予很大的希望的。胜利消息传来,他与大家一样欣喜若狂,以为自由富强的中国要建立起来了。此后他接到邀请,作为天津金融界代表访问重庆。但这次是抱着满腔希望而去,却被担架抬着回来。 当时流行一个谜语——用“抗战胜利”打一古代人名,答案有屈原、苏武、蒋干、共工等等,然大家认为最好的一个答案是“白胜”——白白胜利了,老百姓没得到任何好处。
资公在重庆,目睹的是一幕一幕的“接收”丑剧。特别是他的挚友和同乡前辈——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范旭东被宋子文气死之事,令他灰心丧气。当时永利公司遭到极大破坏,打算从美国进口一套新的化学机器,万事俱备,只待中国银行担保。没想到范旭东与宋子文谈来谈去,最后得到的暗示竟然是只有将公司归他主持才可以得到担保。本已心力交瘁的范旭东心脏病发作撒手归天。资公由希望到失望,由失望到绝望,精神上几乎被摧垮,不幸在归途中染上了极为凶险的登革热。 他被抬至家中,没想到几位北京协和医院的主治大夫已经等候多时。他们并非能掐会算,此次不请自来主要是为了打探重庆消息,阴差阳错居然在第一时间对资公进行了名医会诊。
襄赞之功 从重庆回来后,资公对国民党热情大减,立志不参政。资中筠曾亲眼看到父亲撕毁聘书。但他将参加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当作一生中获得的最高荣誉和最大幸福。 1949年他在一次赴金融界座谈会的途中,看见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的行名已经被纸遮盖,并换了一个银行名字,到会后立即建议要保住这两块牌子为我所用,因为两行在全国的信誉较高,有利于搞好金融市场工作,同时是国际上认可的,这样就为国家保存了在世界各地的大笔外汇。在他逝世后,讣告上对他的生平介绍中有一句话:“对共和国的建立有襄赞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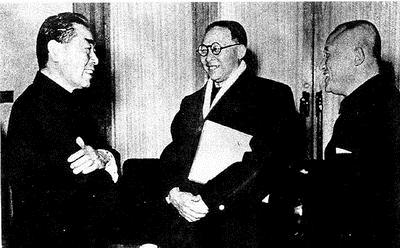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