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建新在天堂过年
冉建新所在的都亭街道办事处既包括利川市最繁华的地区,也有城市扩张方向上正在和即将征收的大量农田。几年来,城市规划与私房传统,房价高涨与拆迁农民无保障的矛盾一直在积累,冲突和上访事件时有发生。冉建新的死亡并不简单是一个刑讯逼供事件,而是又一次关于土地和拆迁的悲剧,这一次的主角不再是拆迁户而是拆迁户这片土地的管理者。
离开利川市繁华的市中心沿着体育路向江边走,沿路两旁的房子并不规整,一式一样。这是冉建新所在的都亭办事处教场村七组的土地,七八年前从老房子翻修成四五层高的水泥楼房,一楼大多做成了商铺或者饭馆,如果不问当地人,从外观上看这里与利川市区已经融为一体。再往前走,教场村八组正在重复着七组的城市化过程,路边既有上世纪60年代之前建造的土坯老房子,也有正在打地基的工地,其他大部分的是已经建好的新楼房,同样是不规整,样式全凭房主自己喜好,但是全都建成了7层半高。
谭平(化名)的房子并不沿街,外观也选择了低调的灰色,但是立在周围鲜艳的楼群中反倒显得现代和特别。走进楼里却没有外表那么气派,楼梯连护栏都没有装,台阶上的水泥没有抹平,墙壁也没有粉刷还裸露着水泥。谭平和妻子住在二楼,门只是一块破旧的薄板,房间里是粗放的大开间,只有一张床,没有家具,日用杂物就散放在地上,墙边砌了一个灶台就算是厨房。谭平告诉记者,这栋房子的造价是40万元左右,除去积蓄和老房子的折旧费,他还借了十几万元,粗粗建好之后实在没钱装修和买家具。但是,他对现状已经很满足了,一楼已经被当做仓库以每年6000块钱的价格出租,楼上的房子也以每层每年3000块钱的价格招租。同失地后毫无收入相比,修房子让他找到一个可靠的经济来源。
这种自己修房子的方式是利川市的传统,当地人告诉记者,原来住平房的时候外面有一个院子,翻修时候就按照院子的大小做成楼房的地基,也有人会在自家的田地里圈地盖房子。教场村八组进行的改造也遵循着这个传统,统一把旧村推平,一推一修之间村里可供建房的土地面积增加了,然后按照每人48平方米的标准重新分配地基。谭平告诉记者,人口多的家庭不全修成房子,而是卖一块多余的地基。现在地基价格涨得很快,前年只要20万元,现在最高能卖60万元了。卖一块地基修房子的钱就有了,不用像他这样一边借债一边修。重庆人王先生买的就是村里沿体育路的地基,不用担心繁琐的手续问题,只要交给村委会3万块钱水电管线工本费和管理费,他就可以在这里安家做生意了。
这看起来利民创收的模式按规定应该经历一番程序,农业用地转为建筑用地,利川市规划局的许可,建设许可,另外如果像王先生这样并不属于教场村人,是不允许私下买卖土地建房的。但是在利川,这些规定一点都不深入民心,整个城市里就像一个大工地,每条街都有人在拆房子和建房子,谁是合法的,谁又是“三违”很难分清。
政府的压力
冉建新是这一区域——都亭街道办事处主任。他负责管理这一带。
2005年,冉建新从利川市司法局局长位置调任都亭街道办事处主任,现在同事们看来,虽然是平级调动,但是属于重用。因为这段时间前后,利川市的财政来源发生了变化。原来国家级贫困县利川只有卷烟厂一家大型企业,烟草行业的税收占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2005年在湖北省烟草行业的兼并重组中,利川卷烟厂与武烟集团合并。失去了烟草这一支柱产业,利川市新的财政来源是立竿见影的土地市场。而都亭办事处的辖区范围是城市主干道清江大道以南的大片区域,教场村、榨木村等有大量待开发的农田,也是城市发展的方向。
2008年,利川市成立了土地储备委员会,由市长担任主任,组成人员还包括国土、发改、财政、建设、规划、房管等部门负责人,冉建新因为辖区的特殊地段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成立之前,以清江大道为轴,利川早期的商品房项目丹桂园、土产小区等都是地产公司从改制的国有企业收购土地,政府只收取一定数目的管理经费,现在土地的收购、储备和出让全部由委员会垄断了。它的效率很高,在2010年公布的财政数据里,2009年利川的财政总收入超过7.3亿多元,地方一般预算收入首次突破3亿元,而这其中有1/3是土地收益。
但是土地财政跟利川长久以来的自己建房习惯产生了矛盾。根据利川媒体报道,利川本地常住人口只有十几万,有七成以上从农民手里买地自己盖的私房。“政府大规模卖地,但是还要保证耕地红线应付国土资源部卫星片区检查,并且减少将来征地拆迁时的补偿成本,建私房的现象就必须严管。”利川一位干部告诉记者。2008年利川政府开始紧抓违规建房、私自圈地交易土地、无资质私自开发房地产的现象,都亭辖区里既是城市的重点规划区,也有宜万铁路、滨河路重点工程建设,是清查“三违”的主要区域。
清理“三违”是一个棘手的工作,从火车站一出来到利川市区,到处能够看到买卖地基和私房的小广告。利川市一个干部告诉记者,利川就这么大,都要在这儿生活,拆别人家的房子本地干部都不怎么积极。而且,花钱买地基建私房的许多都是各乡镇的干部、公务员,这成了整治“三违”工作难以推进的障碍。去年夏天,分管的副市长在“三违”整治会上直接质问是否已经对干部参与“三违”明确“亮剑”——“政府觉得整治‘三违’要先管住干部,干部管好了,老百姓也好管,因此让纪委书记李伟来负责这个工作。”
李伟用强悍的作风压住了一段时间。“三违”办组织了两个班,一共60多人,一天24小时在街上巡逻,看见盖房子的就让停工。但是等他一去党校学习,私房又偷偷建了起来。刹不住违建除了干部参与其中,也因为对于农民来说建私房和卖地基已经不是解决住房问题了,而是找生计。从利川市南部的边界宜万铁路往北到商业楼盘聚集的清江两岸,可以看到大片的农田都已经撂荒,都亭办事处榨木村村民告诉记者,这个区域内的王家湾村、榨木村和教场村的土地已经基本都征完了。村民告诉记者,这一片区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和青苗费加起来每亩地补偿4.15万元,然后就再也没有其他的收入。打通滨江路时,负责征地的工作人员曾经向村民们保证,滨江路修好之后就是一个旅游点,村民也可以做生意维生。可村民花了几万元投资的旋转木马和玩具电动车还没有摆过一个夏天,城管就清理了滨江路上所有的摊贩。
失地农民反对这种没有保障的征地行为。周雄(化名)研究了从中央到利川的关于征地的政策和文件,还把这些内容复印出来给村民们发放,给市委书记写信、上访和向国土资源局申诉。上个月的18日,利川的房地产公司力拓公司到榨木村十组已经征收的50亩土地上建围栏,跟前来阻止的村民发生了冲突。“这块地政府以9800万元卖给了开发商,而我们每亩地才得到3.2万块钱。”村民告诉记者。还有村民用青砖把曾经是自己的、现在已经征收撂荒的土地围起了墙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冉建新所支持的建房其实缓解了这种矛盾。教场村八组旧村改造是赶在政府还没有规划之前占先机,让谭平这样的村民住上楼房,依靠租金过日子,也能通过卖地基给王先生这样外地人的方法得到一笔资金。手里所剩土地更少的七组已经建不了这样的安置小区了,他们在村里不大的空地建起了一栋22层的高楼。生产队没有钱工程款由工程队垫付,等村民们都分到房子之后再分摊所有成本。除了这样生产队组织的建房,都亭街道其他村落还有相当多明确界定的“三违”建筑,龙潭村路两旁错落的房子上都被写着鲜红的“停”字。李伟自己在视察中,还发现了都亭普安村4组的村民私自建设了一条横穿10亩梨园的道路,道路两旁都已经圈占好了土地,准备打地基。
“冉书记说,已经建起来的不能让人拆掉,就建着吧。主要抓还没建的。”村民告诉记者。在“三违”整治中不那么全力以赴的街道办书记冉建新,碰上了铁腕的纪委书记李伟,工作中的冲突不可避免。“冉建新是14个乡镇书记中年纪最大、资格最老的一个,书记们都喊他‘二哥’,他又掌管着市里重要的地区,办他对其他人有威力。”冉的同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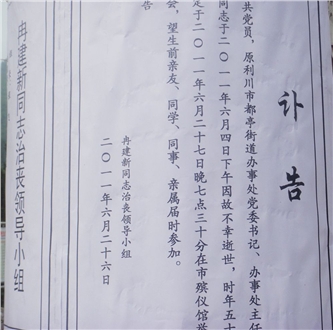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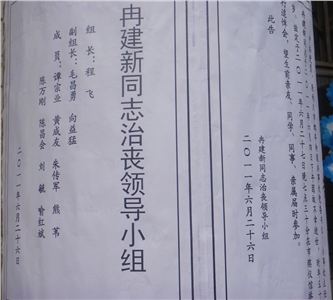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