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的真实死因
1936年5月27日高尔基从克里米亚来到莫斯科。6月1日他去凭吊了儿子的墓地。回到家里,他感到不舒服,体温骤然升高。病情十分严重,以至3—5日之间不得不紧急举行会诊。一位专程从列宁格勒赶来的教授参加了会诊。
可是,6月18日他便离开了人世。时间是2时30分。
一个至今未解之谜一直把6月1日和18日这两个日子隔开……现在就让我们试图稍稍掀开这个死亡之谜的遮盖物。
阿廖沙.彼什科夫从小酷爱捕鸟,长大后也是一个酷爱鸟儿的人。对于他这样一个在一心渴求发财致富却又如同被关在牢笼里的市民阶层那恶劣环境中长大的人来说,与其他人相比,鸟儿更成了行动往来、快速飞驰、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象征———自由的象征。大概,他不止一次地回想起那只被他堂兄掐死了的可怜的麻雀……这是他的自传体三部曲中最具感染力的情景之一。
早在1893年,高尔基写了一篇寓言情的东西:《撒谎的黄雀和爱真理的吸木鸟》。大约过了两年,写了《鹰之歌》。1899年在库列平家里又写了《鹰之歌》的新篇,其中有“勇者的奋不顾身乃处世之道”的语句,后来这语句成了驰名的英雄主义的代名词。
勇者的奋不顾身……是的,他常常表现出这种奋不顾身的精神,现在说起来也还是问心无愧的。然而,常常,是否就是永远?特别是在最后几年……那一幢并不合他心意的百万富翁里亚布申斯基的豪华别墅不是变成一个镀金的笼子了吗?
有个时候,他喜欢在草原上生篝火。后来,在他的一生中始终保持着这个习惯。也许,他最喜欢的还是火光和鸟儿。要知道,篝火可以使他想起那只美丽的正在飞同人所不知的地方的火鸟。可现在,他只能获准欣赏一种篝火———一种缓缓地吞噬着烟灰缸里划过的火柴棍和烟蒂的篝火……
他或许还想起了早在20年代初写给罗兰的那封信。不过一年前,他还在高尔基家里做客呢。
他意识到自己说了不少的话,因而也渐渐地觉得冷起来,尽管说话外表上是快活的样子,但内心变得冷若冰箱。
1936年6月,高尔基感到死神将至,仔细注视起自己,注视起死亡的进程。直到这时,他还希望“跳起来”,再一次坐到那张他已习惯了的写字台(比一般的写字台高,以免控背拱肩)旁去描述发生了的事情……
尽管他并不愿意,但由于种种原因,近一两年来还是越来越多地去想死亡这件事。有一次,他去参观他的一位老相识———杰出的油画家涅斯捷罗夫的工作室。他注意到一幅早在1928年画好的肖像画《水塘边的姑娘》。他十分赞赏这位姑娘全新的心境———不是修道院里那种令人沉闷的心境,而是一种与个人的社会积极性紧密相连的心境。可是,涅斯捷罗夫为他的高尔基家里画的那幅《生病的姑娘》……多半是不可救药的了……
更早一些时候,在详细而关切地回复加米涅夫关于出版《思想录》的来信时,他就对于用唯物论观点编写“流芳百世的思想录”的可能表示怀疑,认为这种思想是教会思想……
但是,他并不怕死。他懂得,死亡不过是从存在到不存在的转化。死亡不是心脏停止跳动的一刹那。死亡,实际上从不愿意生存便开始了……
然而,总的说来,全球性的问题越来越使他焦虑不安。他仿佛要尽力登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期描绘一个完整的世界。他在纸片上扼要地写下了这样几点:
“存在之谜。
“人和宇宙。
“对思维能力之数量与质量的人为限制。
“有机生命在宇宙中的第一个住处。”
作家研究生命直到最后一息。当他已经完全不能从外面用新的事实来充实自己的时候,他便把视线转向自己濒于不存在边缘的灵魂深处。他悄悄地放上一本E?塔尔列的《拿破仑传》———这是他所读过的无数的书籍中的最后一本———拿起一支用小纸片裹着的铅笔来写,而全然不顾标点符号的规则:“东西发沉书籍铅笔杯子一切看起来似乎都比原来的小……”“极其复杂的感觉。两种交替出现的反应连结在一起:神经感觉迟钝———仿佛神经细胞逐渐衰竭———表面蒙上灰烬和所有的思想都黯然失色。
作家离开人世的许多弄不清的情况引起了他被毒死的说法。渐渐地,这种说法在同时代人与后代的脑海里扎下了根。一位很久以前、在本世纪初就和高尔基一起共事,但对俄国发生的事件在认识上存有分歧的侨民鲍里斯.扎伊采夫在50年代初曾强调指出作家死亡的离奇性:“……高尔基?海燕?伊里奇的朋友?那时候,可以想象他曾那么渴望的革命会给他敬上一杯毒酒吗?”
这“一杯毒酒”的概念从此不仅深入俄国百姓,而且深入世界各国人民的意识之中。这正如一位著名的美国问题专家说的,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当代美国读者对高尔基所怀抱的崇敬心情。
但流传得最广的说法,仿佛是斯大林派人给高尔基送去了一盒有毒的糖果。这是被判了25年劳役,后又被流放到北极地带的普列特涅夫教授披露的。
这种说法看起来还真是那么回事(这是作者从著名画家、1966年在纽约出版的《我的会见日志:悲剧系列》一书的作者尤里.安年科夫的途述中摘引出来的。顺便说说,这本书还收入了一篇以极为友善的笔触描写高尔基的特写)。
“1936年高尔基在苏联猝然死亡之谜至今未解,尤其是在关于医生未遂‘犯罪阴谋’被揭露出来之后……
“我相信……普列特涅夫教授的坦白词,他是个有名的医生,曾经和另外几位医生给高尔基治疗……”“我们给高尔基治的是心脏病,可他所感到的与其说是肉体上的痛苦,不如说是精神上的痛苦:他一再以自我责备来折磨自己。在苏联,他觉得没有自由,强烈地渴望回到意大利。其实,高尔基在力图回避自己———他已没有更大的反抗能力了。然而,克里姆林宫那个疑心重重的暴君最担惊受怕的是著名作家公开反对制度。因此,他同平时一样,在必要的关键时刻想出了最有效的法子。这一回,他的做法就是赠送一只精美的糖果盒。是的,一只用鲜艳的丝绸带装饰得非常精美的粉红色糖果盒。总而言之,是美的诱惑!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糖果盒摆放在高尔基床前一张夜间用的小桌子上。高尔基热情好客。这一回,他慷慨地把糖果分送给两位在其身边工作的护理员,自己也吃了几粒。一小时后,三人开始胃痛,痛得撕心裂肺,又过了一个小时,三人一起死亡。立即作了解剖。结果?不出我们最坏所料,三人均因中毒身亡。
“我们几个医生缄默不语。即便在克里姆林宫官方人士对高尔基的死因作出纯属欺骗的解释时,我们也没有予以反驳。然而,我们的缄默并救不了我们。高尔基被谋害的传闻迅即在莫斯科传开,说斯大林把他毒死了。斯大林听到这些传闻心里很不痛快。必须转移人民的注意力,把它置到别的方面。一定要找到别的罪犯。最简单的办法自然是把罪责归咎于医生。医生们因被指控毒死高尔基而被投入了监狱。医生毒死高尔基图个啥?愚蠢的问题!不消说,是受了法西斯分子和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指使。结局吗?结局你们都知道了。”
普列特涅夫的证言最先见诸于德国女记者勃里基塔.格尔兰发表在1954年《社会主义通报》杂志上的文章。她是1948年在普列特涅夫领导下的一个营地医院当医士时与普列特涅夫相识的。他们相识的时间不长,只有几个月。大概是这位年事已高的教授(那时他已78岁)对她产生了好感,也不愿意把秘密带进坟墓,便把秘密和盘托出,告诉了自己的女同事。
关于瓦克斯别格提出的第二个比较重要的论据。他援引了1941年9月2日普列特涅夫和其他许多无辜者在奥尔洛夫监狱地下室被处决的有关资料(当时有154人遇害)。
可是,我们不禁要问,在战争初期,在德国人快速进攻的条件下,哪能绝对地估计到在什么时候处决什么人?也许,在那种条件下,甚至有人想把普列特涅夫作为很有价值的见证人保上来。不过,谁又能知道,哪怕是那个贝利亚。战争的车轮会转向何方?又是怎么个转法?……总之,有关人们悲惨遇害的日期完全是人为确定的,这种事情听得多了。
经过对各种可能因素的思量,我们对格尔兰提供的消息原觉得尚有可信之处,但细细推敲起来,还是感到没有说服力。首先,方法本身就是幼稚的。派人送来糖果,而且还有两个没有任何人证实的护理员的死亡。这怎么不叫人想起斯大林派人给克鲁普斯卡娅送去的那只赫赫有名的大蛋糕!
这么一来,高尔基之死仍然是个谜。
然而,关于高尔基横死的说法却越来越为社会上多数人所公认。一位著名的语文学家B.B.伊万诺夫认为,斯大林与高尔基之死有关是没有问题的。他试图分析迫使领袖迈出这一步的原因。因此,文章取了一个突出的标题:《斯大林为何杀害高尔基?》
这样,便形成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人们从不同的终端去开凿隧道。但两条隧道错开了,在不同的路线上立了一个固定的标记。就像我想象的,暂时没能凿出真理之光。那是不是说,进一步分析和把两种材料、两种论据接合起来的可能一点儿也没有了?不,也许不是汇合(千万可别是性质迥然不同的材料纯聚集物的混合!),而是它们的相互作用将产生一种能最终驱散笼罩着世纪之谜的浓烟的能量。如果说真的有人杀害了高尔基,那么这个杀人凶手究竟是谁?完全按B.B.伊万诺夫那篇文章的标题来理解是幼稚可笑的。
一位曾经给高尔基治疗过的医生M.康恰洛夫斯基写道:“在死前的两天,高尔基感觉非常轻松。这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这一回他的结实的身体一定能战胜疾病的。”
结实的身体……这是不是无意中说错了话,抑或这种说法还有些许道理?
诗人H.阿谢耶夫1927年11月在他第一次到苏联之前半年曾在索伦托拜访过高尔基。他在那里逗留的时间不是一两天,而是两个星期,每天都和高尔基见面。他是这样综述那次和高尔基见面的印象的:“高尔基还是那么年轻,看上去怎么敢不会认为他是40开外的人(请注意,作家那时候已经59岁———巴拉诺夫注)。我这样说不是要恭维他,也不是想净说一些讨人欢心的话。在他身上你根本就发现不了任何好唠叨、衰颓、皮肉耷拉等老年人的迹象。生活使他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他饱经风霜,有着会见、观察、体验等丰富的阅历。”
画家.博戈罗茨基在索伦托逗留期间也不止一次地陪伴过高尔基散步。他证实:“高尔基那时候已经60岁了,但步态非常轻盈(这是不是带有点病态的轻盈!——巴拉诺地注)我甚至可以说,他的步态很优美,很有点像运动员的步子。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尽管背有点驼,但他的体形还是很端正的……”
6月8日,斯大林本人来到高尔基家里。他的到来完全是出人意料的……但又是合乎规律的。
说是出人意料的,是因为他好长时间没到过这里来了,至少也有一年了吧,虽然以前也时常随便到这里来。周围的人都知道,高尔基现在甚至拨不通给领袖的电话———“斯大林同志”每次都是那样地“忙”!
说是合乎规律的,是因为不管个人关系出现过什么复杂情况(在生活中什么事不可能发生!),危难之际总该不计嫌怨吧。现在领袖以高姿态出现,就是要再一次证明,党和政府是器重我国第一位作家的,是热忱而衷心地祝愿他康复的。
自然,高基的病情使许多人不安,其中不少是他的亲属和亲近的人。这为数不少的人使斯大林大为恼怒。他以明显威胁的口吻冲着负责放行的克留奇科夫说:“您知道,我能拿您怎么样?”彼得?彼特罗维奇非常了解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劲地想象得到他的心情。
斯大林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他让所有的人离开(莉波奇卡护士除外),其中也包括高尔基家里的常客,内务人民委员雅戈达,“此人干嘛无事走来走去?”
在雅戈达之后,斯大林紧接着让一个身穿黑衣裳的女人离开。他身穿丧服这一不明智的做法引发了领袖尖酸刻薄的插话:“坐在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旁边那个身穿黑有裳的女人是谁?是修女,还是什么的?……手里光拿蜡烛还嫌不够!”
斯大林兴奋地走到窗前,把小窗推开,一股清新空气涌进房间……
那个身穿黑衣裳的女人就是玛丽娅.伊格纳季耶芙娜.布德别尔格,高尔基的“没有举行过结婚仪式”的第三任妻子。她长期以来故作贞洁姿态,被降到秘书的职位。人们不一定会把那部作者认为几乎艺术活动主要总结的四卷本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献给这位秘书。
获悉高尔基的病情后,穆拉霎时间从她和威尔斯居住的伦敦飞回俄国。
我们知道,斯大林为得到伦敦的档案材料在此之前曾和她见过面。大概,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只不过使他想起……领袖们毕竟也是人嘛……
弥留之际,病人是否意识到是谁看望他来了?还是在长时间的不和之后呢!作家死后,玛丽娅?伊格纳季耶芙娜定会对人说,领袖每一次到来———他探望过病人三次———对高尔基都产生过神奇的康复作用。“他8号那天实际上已奄奄一息,如果不是斯大林来探望,他不一定能起死回生哩。”
于是,8号那天高尔基出人意料地在病床上欠起身子,坐了起来,目光完全是懂事理的。他突然说起话来!他谈到他的创作打算,谈到要写一部《国内战争史》,谈到法国文学的发展……他仿佛是想以其音容使一个人相信,他根本就不打算死,所以才得了点小病。而计划,是这样的紧迫和庞大。
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连斯大林也在内。他吩咐拿来一瓶酒,要为亲爱的阿残克塞?马克西莫维奇的康复干杯。
10日夜,斯大林第二次来看望高尔基。病人在睡觉。曾经迎接过客人的布德别尔格(就是斯大林把她当做“修女”赶出去的那个女人),不许任何人来看望高尔基。
连斯大林也不许?一个绝对的独裁者啊!但现在好像是他已经知道,迎接他的是高尔基的妻子,她正在保护他的安宁(若不是妻子,谁拥有这种全权,甚至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因此也就依了她……
早在1919年,玛丽娅?伊格纳季耶芙娜就来到克隆维尔斯基大街高尔基家里。在此之前,她是被指挥为组织阴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英国间谍罗克哈特的情人,1918年在莫斯科被捕,因罗克哈特是英国国民,被免予惩罚(利特文等人在伦敦可能遭了一阵子罪)。而在那个时候,像她这样的人,随时都是有可能被镇压的,谁也预料不到她的命运会怎么样。但不知何故,她竟能博得直接参与逮捕罗克哈特的有名肃反工作人员佩捷尔斯的好感,甚至比罗克哈特更早一些时候获释。
穆拉具有非凡的毅力、胆量和进取精神,懂得好几种语言。她喜欢捉弄命运、干冒险的事。这些玩艺可以激起她的某种狂热,就像一个赌徒,一旦遇上诱人的可以赢光庄家大把钱财的机会,便会磨拳擦掌,跃跃欲试。再者,正如别尔别罗娃所断言的,穆拉对色情很在行,非常善于利用它……
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眼里,高尔基看起来绝以进个“大红人”,是列宁的朋友。所以,尤登尼奇马上就要进犯彼得格勒的时候,大量的信件,说得更准确些,一只只装有打成活结的绳子的信封寄到高尔基的寓所就是预料之中的事。然而,“革命的海燕”当时向友人诉说的全都是关于布尔什维克“他们”的事,关于为被捕的知识分子张罗的事———为了他们,高尔基同苏维埃进行不懈的斗争———是不能说出来的。因此,完全不能排除玛丽娅.伊格纳季耶芙娜在克隆维尔斯基大街家里的时候就接受了肃反工作人员关于做他们的人,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情报的建议。那时候是非常需要这样的情报的。而高尔基一气之下,1921年到了国外。1922年他在国外反对在莫斯科开始的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22年在卢比扬卡开始了对他的“专案”审查。
正如别尔别罗娃所描的,玛丽娅.伊格纳季耶娜女士正式以秘书———而实际上是以妻子的身份住在意大利高尔基家里的时候,便定期到“爱沙尼亚孩子们”那里去,而且一去总是呆得很久。她神出鬼没,捉摸不定,今天你以为她到什么地方去了,但在那时大使馆根本就见不着她的影子……明天你在索伦托可能收到盖有塔林邮戳的信件,可是发信的时候,玛丽娅?伊格纳季耶芙娜正在柏林呢……
不管怎样,当局仍然认为有必要了解高尔基的思想趋向,了解他经常与之来往的人。谁能够提供这样的情报呢?在外国的环境里,只有作家最贴身的人了。逐一想想高尔基家里所有的人,你就可以得出结论:这样的间谍只有玛丽娅?伊格纳季耶芙娜才能充当。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生病之后,布德别尔格迅即从伦敦飞回。她是从谁那里,又是怎么得知高尔基的病情的呢?据说,是家里的人叫她回来的。是谁?是高尔基的第一任妻子E.彼什科娃吗?30多的前他们便分了手,只是保持亲热的友好关系。未必是她。此前,儿子已经不在人世了。是不是儿媳季莫莎呢?也不一定真实。那么,主要的是,事情是否征得了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的同意?只要回想切尔特科娃关于高尔基在克里米亚就和她破裂、甚至不愿接她的电话的证言……也是非常令人怀疑的。那会不会是他9岁的长孙女呢?
再说,她是怎么获得英国当局批准这次旅行的呢?通常,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有时解决一个问题得耗费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况且,当时和伦敦航空通信是受限制的。连别尔别罗娃都尖刻地嘲笑这一点,认为乘坐飞机回来是难以置信的……
自然,迅速飞回俄国对“男爵夫人”是极有好处的,因为她想获得继承作家在国外那笔稿酬的文件的签署。但世她的到来也许对男一个人比对亲属更有好处。这不能不同意巴拉霍夫的看法。他写道:“布德别尔格畅通无阻的往来使那些最为隔离作家一事担心的人产生了保护的想法……”然而,大家早就知道,这种隔离对谁最为有利,这种隔离又是根据谁的旨意来实施,把屋子变成了“金笼子”的!
斯大林知道,玛丽娅?伊格纳季耶芙娜和高尔基的关系实际上已经破裂,她一定会很快就同意迈出这一步。而且,其结果对于她本人来说将是最为有利的。不是吗,无论从正式关系还是从法律上看,她对他来说什么人也不是。但是大家都知道,阿列克塞?马克西墓维奇非常爱她,希望她的生活靠他国外那笔稿费得到保障。玛丽娅.伊格纳季耶芙娜若能占有一席名正言顺之地,她肯定会被吸收参加高尔基文稿审定委员会,同时为妥财务手续…
斯大林的这一次行动计划,如同天才领导者其他所有计划一样,是经过周密考虑的。赶走雅戈达,是为了使特工机关免受怀疑。假装认不出“修女”穆拉,是以防有人怀疑她参与这一勾当。为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的康复而干杯的那一瓶酒呢?领袖是不怕任何毒药的。至于穆拉在病人房间,要把这里的一切安排停妥,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只要从斯大林办公室打个电话给吓得魂不附体的克留奇科夫,让他严守秘密地转告: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并不知道被他叫走的那个女人是作家的妻子。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对发生的误会深表歉意,并且认为,正是他的妻子才有守候在病人床前的优先权,如果这能加快病人康复的话。请转达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对尊敬的玛丽娅?伊格纳季耶芙娜最良好的祝愿……
总之,高尔基离开人世了,而穆拉还过了多年无比快乐的生活,并多次到了苏联。我记得,作家的另一个爱过游乐生活的孀妇柳德米拉.伊里伊尼奇娜?托尔斯塔娅曾以毫不掩饰的满意心情对我说:“我要和玛丽娅.伊格纳季耶芙娜乘坐轮船游览伏尔加!”
问题是,最后几年斯大林与高尔基的关系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原因变得极其复杂起来。大概斯大林最为忧虑的是高尔基拒绝写颂扬他的书。即使不写书,为《真理报》写篇《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也好嘛。A.奥尔洛夫在《斯大林罪行秘史》中写道:“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人深信,这一回高尔基不可能再逃避写作的旨意了。但是,他比他们所预料的更具原则性,他辜负了雅戈达的期望。”
在高尔基这本日记落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手里之后,雅戈达仔细地了解了日记的内容,含糊不清地大骂了一句:“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显然,他在高尔基的日记中找不到任何指望实现领袖夙愿的根据。
综上所述,我想,绝大多数研究人员(包括JT.斯皮里多诺娃的最新专著《马.高尔基:和历史对话》,苏联科学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版,1994年)不同意的所谓“自然死亡论”不复存在了。其实,亘古以一它就注定是这样的。
不过,我们可以再设想最后一种有利于这种“自然死亡”观点的不同说法:没有目击者关于高尔基的病情和死亡情况的直接证言,有的仅仅是纯医疗上的记录。可是,有了我们所知道的高尔基在笼子般的屋子里生活的情况,有了我们所知道的高尔基在笼子股的屋子里生活的情况,有了我们所知道的他儿子被刹害的情况,有了我们所知道的他与党内反斯大林的派别同专制制度与封锁日益抗争的情况,以及斯大林为彻底“打掉”那些阻碍他不惜任何代价全面歼灭各种异己思想的人而采取的策略,等等,等等,难道有了这一切还不足以令人确信高尔基必定是领袖的受害者么?
“自然死亡论”使高尔基的道德形象受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显然,在重新唤起对艺术大师高尔基的兴趣之前,必须使他有机会得以恢复作为一个有道德的公民的名誉。
可喜的是,他已经获得了,或者说他在饱经痛苦之后已经得到了恢复这种名誉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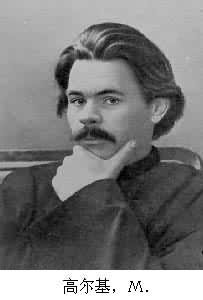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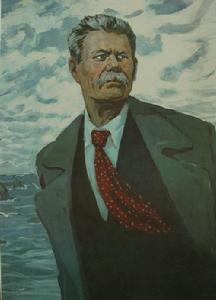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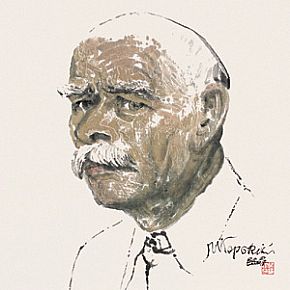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