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忆良缘
西方习俗,结婚十年为锡婚,二十年为瓷婚,三十年为珍珠婚,四十年为红宝石婚,五十年为金婚,六十年为钻石婚。本书大约是历史学家周一良(1913-2001)的最后一本著作,以他与老伴六十年共同生活为线,回忆了他的丰富的经历和复杂的心境。本文摘自书中第三至六章。
初识邓懿
我小时在私塾读书,没有数理化的基础,不可能考大学,而兴趣又在国学方面。清华国学研究院当时已停办。燕京大学有专门训练中学国文老师的二年制国文专修科,入学不问资历,只考国文、历史。我于1930年秋进了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但专修科不是正途出身,我很想转学。
刚刚成立的辅仁大学查验文凭比较松,当时造假文凭风甚盛,我在琉璃厂假造了一个安徽高中的文凭。同时,辅仁入学考试也比较松,数理化中只考数学一门,我就请我的表兄孙师白替我去考,就这样进了辅仁大学历史系。
新开办的辅仁大学,对于一年级的课程很不重视,我感到不满足,又思转学。而燕京大学转学是只考国文、英文两门,我当然优为之。这样,我以辅仁大学一年级生的身份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
次年春,学生会组织去泰山旅游,我开始与邓懿相识。她毕业于天津南开女中,各门功课都很好,尤其喜欢文学。
30年代,天津有一家名叫《北洋画报》的刊物,是赵四小姐的姐夫冯武越所办,雅俗共赏,颇受欢迎。该刊每期的刊头上都是一位女士的玉照,或两位女士的合影,其中有电影明星,如胡蝶、阮玲玉等,或者就是当地的大家闺秀。邓懿的照片就经常上《北洋画报》。
我是从外校转来的二年级学生,按规定必须补修一年级的中国通史,由邓之诚先生讲授。当时邓懿是国文系一年级学生,也在这个班上,不过我们没有交谈过。1933年春到泰山旅行时,我们开始有了接触。邓懿为我在虹桥飞瀑拍照。照片洗出后,我送给邓懿一张,背后附题记“廿二年春游泰山邓懿同学为我拍因赠一良”。后来我的钱包和大衣被土匪抢走,当时认识的天津同学只有邓懿,于是就向她借了五块钱。回天津以后,上她家里去还钱,才逐渐对她的家世有所了解。她的父亲于清末留学日本学法律,回国后做了律师,同时也靠吃瓦片(做房东)有所收益。他还是一位诗人。我和邓懿的家庭背景和文化教养都比较接近,谈起来有很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比如我们都喜欢听顾随先生的课,都喜欢看京剧,都喜欢听刘宝全的大鼓书,等等。
名媛青眼
邓懿在燕京颇引人注目。据说她刚入学时,就有一位同班同学追求她。那人西装革履,对她百般逢迎、千依百顺,反而引起她的反感,断然拒绝与他交往。而我呢,一身蓝布大褂,像个老学究,不穿西服,——事实上,我家里也从未给我做过西服。我每学期从家里带二百块钱到学校来,除交学杂费和伙食费以外,所剩无几,没有多余的钱做衣服。直到我有稿费收入以后,才做西服穿。另外,在我与邓懿的交往中,决不唯命是从、唯唯诺诺,倒是经常与她发生争论,这也是与那位男同学大不相同的地方。或许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吧,邓懿对我似乎较有好感。
就这样,一来二去,我对邓懿逐渐由最初的好感产生了爱,但她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有一天晚上,我陪她从图书馆回到女生宿舍二院门口,就在我们即将分手时,我毅然决然地用动作明确表达了我的爱情,我的这种冲动对她来说大概有些意外,又似乎是在意料之中。恰好这时钟亭的钟敲了三下,是九点半(此系采用西方海上报时方法)。当时我们都在学法语,因此事后常常用法语“neufheureetdemi”提起这个时间。当时邓懿对我表示,由于她父亲过早去世,母亲又体弱多病,弟弟、妹妹还年幼,她必须主持家务,不能结婚。我的回答是,这一点也不成问题,对于她的母亲,我是会负责到底的。四十年来的事实证明,我实践了当时对她许下的诺言。
当时燕京大学规定,女生宿舍的一、二、三、四院男士免入,男生来访只能在门口按铃,请女生出来谈话。女生宿舍的北面有两座小楼——姊妹楼,靠北面的那个小楼,就是专门为女生预备的会客室,屋内摆放着许多沙发,沙发的靠背都很高,是为了方便学生躲在沙发背后谈心。燕京大学的校园非常美丽,湖光塔影,草坪上、柳阴下、湖水畔、钟亭边,无处不可留连,都是情侣们谈情说爱的天然胜地。记得俞平伯先生曾经说过,清华园好比是一篇散文,而燕园则好比是一首诗。燕京的学生可以说是在诗一般的环境里学习和生活的。
此外,还有一处情侣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就是燕京大学东门对过的常顺和饭馆,饭菜可口,而价钱不贵,环境也比较干净。男生们常在此宴请女生。直到今天我还能数出常顺和的一些菜名,如糖醋溜松花、焦炸土豆丝等。说到这里,我可以再举出一件邓懿与别的女生的不同之处。通常男女同学出去吃饭,理所当然地是由男士付账,而邓懿遇到这种情况,总是和我争着要付账,由此可以看出她所具有的那种独立自主的新女性精神。
甜甜酸酸
前面说过,邓懿在大一时已经拒绝了那位追求她的男生,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警惕,甚至变得有些疑神疑鬼。邓懿有一位很要好的女友,论才论貌都远不如她,这位女友有一位燕京毕业的表兄,一表人才。他们三人很谈得来,常在一起。当时虽然听说那位表兄对他的表妹很中意,但让我觉得蹊跷的是,为什么他在如此优劣悬殊的两个女友中,不“择优录取”呢?我一直为此怀有醋意,感到忐忑不安。直到那位表兄最后与他的表妹结了婚,才消除了我的担心。
我把1933到1938年这五年恋爱时期概括为甜甜蜜蜜的五年,在甜甜蜜蜜之中掺入一些酸味,也许就更显得甜蜜了吧。
在我这方面虽然没有使邓懿感到疑虑的事情,但遇到过一些人为我提亲说媒。初入燕京时,我的姨母就曾想把我舅父的女儿说合给我。当时不懂什么近亲不婚的道理,但认为婚姻大事应当由自己选择,所以婉言谢绝了。还在燕京国文专修班的时候,容庚先生曾想把他的得意弟子、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女生介绍给我,先从侧面了解她的想法。这位女生表示,她将来非博士不嫁。后来她果然嫁给金陵大学的一位教授刘博士了。此事是多年以后朋友讲给我听,我才知道的。可是,周一良以后不也成为博士了吗?
恋人之间不管如何相爱,总不免会有一些摩擦和误会。有一天晚上,我和邓懿在二院女生宿舍门口,因为有什么事情存在误会,没有能够澄清,可已经到了关门的时间,只好分手了。我那时忽然想起黄仲则的两句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于是就想试一试“风露立中宵”的滋味,在二院关门熄灯以后,仍在门口独自徘徊不去。后来校卫队来巡逻,觉得我可疑,经过一番盘问以后,就把我带回男生宿舍去了。
兴趣同异
1935年夏,我从燕京毕业。那个暑假我没有回家,留在学校,和邓懿两人花前月下,尽情享受恋爱的甜蜜。1935年秋,我入燕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院,主要目的就是再呆一年,等她毕业之后,再一起离开燕京。就在这一年冬天,我们在正昌饭店宴请师友,宣布订婚。
另一方面,这一年我在学术上有极大的收获,这就是偷听了陈寅恪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课,眼前放一异彩,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决心走他的道路。1936年,经陈先生推荐,史语所聘请我去工作。接受陈先生指导和搞研究工作,这两个条件对我而言都是求之不得的,我当然极愿意去。
此时,邓懿从燕京大学毕业,我对邓懿所学的专业中国文学很感兴趣,她写的毕业论文是纳兰性德词,而我也很喜欢读《纳兰词》。现在她手边还保存着一张纸条,是我用毛笔写给她的短笺:
《宋名家词选》奉缴,曾略读之,误字颇多,惜未能一一勘出也。书中犹存牡丹一瓣,良以买珠还椟,意有未安,特留此最艳丽者随书奉还,敬希纳。明早课毕望即至校门,一良当在彼恭候也。郭家晚饭如何?小萝晚佳。一良八点半。
可见当时我们两人在这方面的共同兴趣。但从她那一方面来说呢,对我的历史专业可说是一点也不感兴趣,认为历史学枯燥无味。我这一生所写的东西,恐怕她只读过自传《毕竟是书生》以及我污蔑她是漏网右派的大字报。她从来没有从头到尾读过我任何一篇学术论文。
当时我们印制了带有红叶标志的信纸和信封,所以弟妹们每看到邮差递来带有红叶标志的信封,就大嚷大叫地给我送来。
中西合璧
1938年4月3日,我们在天津结婚。
法租界的国民饭店建于20年代,是当时天津最大的饭店,号称可以举行数百人的大型宴会。我们是在国民饭店举行的婚礼。30年代的婚礼可以说是中西合璧,先在饭店里用西方方式举行,然后再回到家里按中国传统礼俗重来一遍。
西式婚礼中,证婚人是很重要的人物。本来想请傅增湘来证婚,因为他是当时文化学术界的头面人物,同时与周、邓两家都有渊源。但因平、津之间交通不便,所以改请了开滦矿务局的总经理孙章甫先生。孙是美国留学生,同时又是与我们有亲戚关系的前清学部大臣孙家鼐之孙。
新郎和新娘的衣着都是西式的,新郎黑色礼服、白手套。新娘白色衣服,长纱委地。新娘手里拿的花束是自己设计的,用白色马蹄莲扎成。结婚前一天,我们到一家白俄经营的利佛西茨照相馆照了相。当时还准备了一个精美的小纪念册,由我十岁的小兄弟景良拿着,请来宾签名。
婚礼结束后,客人入席;而新郎、新娘回家,脱去西式服装,新郎换上长袍马褂,新娘上身穿花色短袄,下系红裙。两人先拜祖先,后拜父母,然后向来宾中的长辈行礼。新房里挂的礼品,有傅增湘送的对联,还有顾随先生写的条幅:“屏除丝竹”。桌上陈列着同学们赠的礼品:谭其骧《中西回史日历》;邓嗣禹《居里夫人传》(英文);侯仁之、张玮瑛《牛津诗选》(英文)等。
太平洋战争以前的天津租界相当平静,因此我们婚后的生活是比较恬静安稳的。我在当时读的有用书斋刊本《六朝文》上题写过这样一段话:
此书刻印皆极精工,纸张亦好,殊为悦目。廿七年孟冬予以病后静养,不能治史,因取是册与室人萝厂共读之,期以能背诵而后已,亦怡养性情之一道也。惟予藏此书止存上卷,盖有赵中令半部《论语》治天下之意。十一月十二日灯下,一良识于泰华里寓庐屏除丝竹之室,时萝厂在侧,为予制无缝之天衣,炉火熊熊,一室皆春。
这段话基本上可以代表我那一时期的心境。
(贺春摘编)
摘自《钻石婚杂忆》周一良著三联书店2002年5月版
《文汇报》2002年7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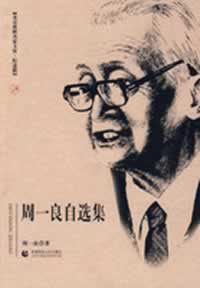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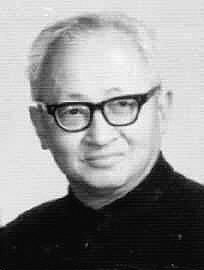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