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眼中的周一良
汪荣祖:长使书生泪满襟
我初知周一良的大名,早在台湾大学读书之时。那是50年代末,海峡两岸紧张对峙,音讯隔绝,台大历史系的少数同学从香港侨生之中,得以偷偷传阅大陆学者的著作。我当时已喜读陈寅恪的书,当看到周一良与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时,感到颇具义宁学风而印象深刻。
直到大陆改革开放,中美建交以后,我于1981年得到美中交流学会的资助,到中国大陆访问研究半年。那年秋天,我来到美丽的北大校园,在临湖轩的座谈会上,不意见到一位穿着深蓝色毛装(原是中山装或列宁装)的白面书生,看起来仍是中年人模样,经介绍后才知道是老前辈周一良先生,这不期而遇令我喜出望外。他愿意见我这个后辈,主要是听说我于1976年在香港出版了《史家陈寅恪传》。
此后,我与周先生时通音讯,并互赠书文。1988年广州中山大学召开陈寅恪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参加,使我与周先生有重晤的机会。周先生在研讨会上发表了内容丰富的主题演讲,记得他特别对陈先生自谓“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提出很细致的看法。陈寅恪能运用一二十种外语,熟悉西方文化,怎么可能思想局限于咸丰、同治时代,议论与曾国藩、张之洞相似呢?的确是令人困惑的问题。我在写陈传时,觉得陈寅恪的思想固然与革命相左,但绝非保守,实承袭了其父、祖的变法维新思想,乃于陈传的第二章“思想在同光之间”述之。一良先生于讲演中,很客气地说我的说法是合乎实际的;但是他的精细以及朴学的素养,决不能放过为什么陈先生自己明明说是“咸丰同治之世”。周先生指出,曾国藩卒于咸丰十一年,正与下一句议论近似的湘乡相对应。换言之,陈寅恪自称其思想与议论不出乎咸丰时代的曾国藩以及同治时代的张之洞。周先生谦称“这仅是毫无根据的臆测,有待进一步的探讨”,而我当时听后就觉得很有道理,并启发我进一步想问题。民国以后,曾国藩与张之洞固然都成了过时的保守人物,然而在咸同之世却走在时代的前头,代表温和而讲实效的改革派。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在同光时代都主张变法维新,但与康梁一派实同中有异,并不赞同康梁较为理想而急进的做法,且认为戊戌变法如由李鸿章、张之洞主导,成功的机会要大得多,所以他们的思想与议论实属咸同以来的温和而讲实效的改革派。陈寅恪于民国成立后二十余年,目睹辛亥革命后之乱象,内乱外患更甚于前,思想与议论倾向温和而讲实效的改革,也就不足为奇。后来我写了一本《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其中说到在咸同时代郭嵩焘与陈宝箴父子关系密切,思想议论极为相契。周先生看到我的书之后,于1994年2月28日回信中说,“读尊著后益信陈寅老标出咸同之世为有用意,盖自别于南海也”。这是很有深度的看法。
陈寅老类此思想与议论很容易被认为有“怀念前朝”之嫌,但他绝不是保守的复辟派,决不至于怀念满清政权,而是怀念前朝犹存的传统文化与儒家伦理。这种“怀念”无异形成一种牢固的心态,周先生于1991年5月20日惠函中有极为深刻的体认,“记得适之先生曾说,寅老有遗少味道,一良以为并非全无根据,如挽观堂诗中‘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之类,非对清室有一定感情者,不可能对观堂有如许之同情。一良回忆儿时情况,家父虽早服膺西方学术,曾译康德著作,但有时亦流露出‘遗少’味道。渠与寅老年龄相仿,又皆为清末督抚之孙,宜其思想心态有相通之处。估计北伐之后,遗少心态始渐消失,寅老在观堂挽词之后,似未再流露,而家父晚年竟成共产党之朋友矣”。
周一良先生和蔼可亲,为人非常坦诚,向不掩饰。他的兴趣很广,再加上为了国家的需要而钻研新的课题,学术范围因而包括魏晋南北朝史、佛教史、亚洲史、日本史、中日交通史、敦煌学,以及世界史等好几个大领域。不过,我相信魏晋南北朝史一直是他内心深处的最爱。他早年受到邓之诚与陈寅恪两位先生的启发而醉心这一段断代史,很想走陈寅恪的路。以今观之,陈门诸公之中也只有他最有潜力继承义宁衣钵。他的两本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以及札记,绝非仅仅为乾嘉作殿军,实可与唐长孺先生并称为义宁之后的祭酒。当然我们不免要想像与感叹:如果周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不曾中断30年,则此一学术园地的耕耘,必定会有更多惊人的大收获。
田余庆:“联盟”是我的荣幸
周先生青年时已是魏晋史名家,在我与他交往中他却从不以师道自居,也不多议论专业学术问题。他对我的影响毋宁说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去年,周先生曾让我用他准备的色纸写点什么,我写的话有两句是“蜗行龟步自成趣,为有前头引路人”。周先生确实对我起着引路作用,只是他不好为人师,所以没有多少言论可以记述。周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中说到80年代以来他在历史系与祝总斌先生和我三人“形成系内魏晋南北朝史方面松散而亲密的联盟”。此事是我与祝先生出于对周先生的敬重,希望他能领着我们开展研究而向周先生提出的,多少有拜师的意味。周先生当时用“松散的联盟”五个字一锤定音。至于“亲密”一词,对我说来,也是荣幸。
90年代以后,周先生魏晋史方面的工作做得少了一些。他曾对我说过要写两篇比较宏观的文章,题为《梁武帝及其时代》和《孝文帝及其时代》。前一篇写成了,发表在《历史研究》上,后一篇似乎放弃未写。
回顾半个世纪以来,我真正认识周先生功底深厚,学问渊博,是“文革”以后的事。个人学术接触增多是最主要的原因。改革开放后也更多地知道他的师友对他早年的评价。周先生姓名常出现在40年代胡适、傅斯年、赵元任、杨联等人的信札中,几乎都是对周先生的称赞。以后还看到过其他一些域外史家对周先生的推许。且举较早的赵元任致傅斯年函为例,赵提到战后招致人才之事,说:“史语所要newblood,周一良是第一个要紧的人,万万不可放去。”这样的舆论周先生自己是知道的,但是从未听他说起过。80年代后期的某年,周先生同我聊起台湾竞选院士的事,说到在美国的邓嗣禹教授曾致函台湾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先生,推荐周先生为院士。吴复邓函说,周先生是中研院旧人,大家对他的学问都很熟悉。只是碍于海峡两岸关系的现状,不便在台湾提出此事。邓把此事告诉周先生,周先生淡然处之。
王永兴:213房间的由来
我和周一良先生相识,大约是在1946年的冬天。当时,我是恩师陈寅恪先生的助手,朝夕侍读先生之侧。一日,有人敲门来访,我去开门,他说:“我是周一良,来拜见陈寅恪先生。”按惯例,客人通报姓名后,我要请示寅恪先生,是否应让客人进来。但由于我已久闻一良先生大名,于是不再请示,就请一良先生进来了。我看到寅恪先生笑容满面地迎接他,他们谈话时间相当长,内容主要是寅恪先生问在美国的清华旧日友人的情况,如赵元任先生、杨联先生等。一良先生问询寅恪先生的健康情况,并告诉寅恪先生,他已回燕京,又说此后要经常来向寅恪先生请教。1947年秋日的一天,一良先生又来拜谒寅恪先生,告诉说他已被清华外文系聘为教授,住在新林院。我送一良先生出门时,他邀请我到他家畅谈。此后,每隔三、五日,一良先生就来看望寅恪先生。
第二年春节,我到一良先生家去拜年,谈话中涉及唐史和敦煌学研究,我发现他对中外学者尤其是外国学者对敦煌学的研究成果颇为注意并极为熟悉,我很敬佩。
这一年春节后,寅恪先生嘱我到当时的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先生家,向雷先生提出,他希望将一良先生调入历史系。果然不久,一良先生到寅恪先生家中说,他已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
此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进行了院系调整,一良先生忙着筹建新北大的历史系,我和一良先生见面的时间就减少了。1958年,在反右运动中,我受到株连,以控制使用之名,被遣送到山西太原。又过了一段时间,就来了民族的空前灾难十年浩劫。
1978年,北京大学调劫后余生的我到历史系任教,我住在当时的29楼。报到后的次日,早饭后,一良先生到29楼来看我,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之事。一良先生坐下来,流下了眼泪,接着就失声长恸,我也潸然泪下。之后,他问我,关于他的未来的种种传说,我是否听到过,是否相信,如谋求当时的教育部长之类。我告诉他,我以及在太原的北大清华友人,都听到过关于他的种种谣言,但我们都不相信,因为我们坚信一良先生是个学者。我说一良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已有重要成就,应该在这个基础之上闭门读书,为民族国家的学术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久之,一良先生平静下来,问我到北大后生活工作的种种安排,并问起我的藏书,得知全被焚毁后,他把自己珍藏的寅恪先生赠送的《秦妇吟校笺》送给了我。几乎将近中午,一良先生才离开,我的心也久久不能平静。
此后,我和一良先生均投入了各自的教学科研中。一良先生著述甚丰,成果卓著,同时还为历史系的发展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如加强历史系与海内外的学术交流,请日本著名学者池田温、谷川道雄来系讲学,都是一良先生进行联系的。在我的教学科研中,一良先生也给了我许多帮助,我最难忘的是申请使用图书馆213房间事。
我在北大讲课主要是两类,一是隋唐史,二是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我讲敦煌吐鲁番文书课的方法比较特殊,要用到大量的参考书、参考资料,因此就需要有一间专门的为我讲课辅导学生的房间。为此,我几次向图书馆申请,但都得不到允许。据馆领导告诉我,中国教授一个人不能要房,必须两个人才有可能。于是我找到周一良先生,向他说明我要请他和我两个人要一间研究室,一良先生慨然应允,而且向我说明,这一间房完全由我使用支配。我在213工作了七八年,我辅导学生,给学生改作业,都在213中,如果没有这间屋子,我的工作就无法进行,我非常感谢周一良先生对我的慨然帮助。我能够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教学中顺利进行并完成任务,学生们能够最终写出高质量的读书报告并以论文形式发表,都是和一良先生的帮助分不开的。
2000年夏天,忽然有一天,他家里打来电话,说一良先生已坐车来看望我了。不久,汽车开到门前,周启锐扶持一良先生下车,上楼到我们家里,我们长时间地握手,久久不放。一良先生更瘦弱了,但仍谈到学术研究,谈买书,谈我们的已经去世的老朋友。此后,内子锦绣几次去一良先生家,帮助带书、送书等,我则与一良先生多次通电话,但没想到那一次竟是我和一良先生的最后见面。我望着我与一良先生在寒舍的合影,不胜潸然。
摘自《载物集——周一良先生的学术与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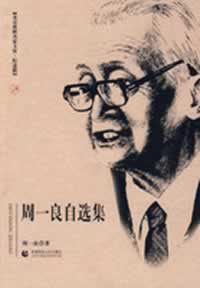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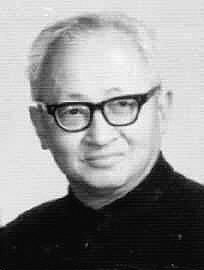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