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毓瑚学术业绩
王毓瑚教授的学术业绩
——一位中国经济史学家兼中国历史地理学家的科学成就
作者:安希伋
载《王毓瑚论文集》
王毓瑚教授(1907—1980)于1949—1980年间执教于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前身),主要研究并讲授中国经济史和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史—古农书研究。王教授从事的学科与我学习的学科相邻,却不相同。其实,早在1937年,我在原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念大二时,我班课表上有一门经济学理论课,主讲教师为王毓瑚教授。因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王教授正在北平,交通阻隔,未能返校,致使我接受王教授系统讲学的大好时机失之交臂。不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有幸以类似传统私塾的方式,受教门下。特别是他的治学精神与处世态度对我产生了深刻影响。兹值王教授文集即将出版之际,又逢王师25周年祭日,借此机会,我粗略补习了王教授中国经济史著作中的若干文稿(含中国农业经济史),于是就不顾外行之嫌,写了这篇短文,主要是记录王教授有代表性的著作和学术业绩,也说一点学习感受(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部分请见《王毓瑚文集》附录中杨直民:《王毓瑚传略》)。
王毓瑚教授早年留学欧洲8年,先后就读于德国慕尼黑大学与法国巴黎大学经济系。完成学业后,于1934年回国,随即投身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直到晚年弥留之际。
回国之初,王教授于教学之余,翻译了两本经济学著作:一是奥地利人Spann,O.所著《经济之四种基本形态》(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另一本是德国人Sombart,W.所著《经济学解》(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次年又作为汉译名著再次印行)。20世纪3O年代,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发展前期阶段,市场运行机制有待改进,也需要借鉴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经验,这两本论述市场经济理论的译著出版,可谓恰逢其时,有助于我国市场经济规范化与健康发展。王教授晚年,正值我国开始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他又把法国人Marcel Mazoyer所著《开发自然界农作制的演进与分歧》一文译为中文,也有外为中用之意。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王毓瑚教授花了大量精力研究中国经济史。早年著作有:《秦汉帝国之经济及交通地理》(1943年),《中国经济史资料》(40年代与傅筑夫教授合编,80年代出版“秦汉三国”等编)、《隋唐两代的钱币》(1948年)、《中国农业经济史大纲》(1950年前后)等;晚年王教授主要著作有:《我国历史上的土地利用》(1975年)、《中国农业发展中的水和历史上的农田水利问题》(1975年)。《我国历史上农业地理的一些特点和问题》(1978年)、《读〈史记·货殖列传〉杂识》(1979年)等。从上举著作可见,王教授跨越学科广阔,又以历史和地理两科为核心。王毓瑚教授治史,既取材于正史,也重视非正史资料。先后撰写了数十篇论文,或为断代史。或为专题讨论。多方考证,进行分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种相关因素,务求确切。他的著作,多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从客观经济规律着眼阐述并分析经济现象及历史过程。我认为这是王教授治史的一大特点。王毓瑚教授的学风,在他为《史记·货殖列传》这篇历史名著作注释并进行研究和评论中,集中体现了出来。他认为,研究司马迁这篇著作,“应当抛开一切个别字句上的纠缠,改从大处着眼,……抓住作者立论的实质”。并指出:“太史公在这里讲的是春秋以后大约三个世纪中的世事变局。此所谓‘变’,是改变了受宗法制度的约束的那种死板的、静止的古代封建社会的局面。一切都变得活动了,首先是人的经济活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从种种礼法规范清规戒律中冲出来了,从而出现了一种崭新的自由活动的世界。”太史公把这个自由、活跃的世界归结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并追述了战国以来上下追逐财富的各式各样的经济活动方式以及一般人的思想意识变化。还列举了一连串成功的产业活动家的事迹。总结为:“富者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优胜劣败取代了世袭制度。王教授指出,在惟利是图原则下,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不再是出身,而是个人所掌握的财产。在封建秩序没落之后,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格局,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伦理观念。他对《史记·货殖列传》一文评价说:“在短短的篇幅中,有理论,有史实,有经济地理,把几个世纪当中波澜壮阔的社会变化夹叙夹议地描绘了个淋漓尽致,这确是一篇大文章。像这样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议论和铺陈,在我国旧的史书中堪称空前绝后。”并认为:《史记·货殖列传》的论点,“与西方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时期在经济方面的理论是极其相似的”。
不过,王毓瑚教授并不完全赞同太史公的观点.主要有两条,一是不同意太史公“工不如商”的论点。在所论3个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商业确实起过很大作用。但是从较长期来看,经济支柱毕竟是产业,而不是商业。没有产业的发展,财富又怎样转化为资本呢?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商业也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即发动了产业革命,不断继续积累资本,发展经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从秦汉以来“走向了单纯以赚钱为主而忽视生产的路线,而且历时多少个世纪始终没有转向的机缘。此中原因何在,这应该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个主要课题”。第二条,王教授不同意太史公说的“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的论点。王教授认为:这只是说“富”可以比得上“贵”,而不是说“富”要代替“贵”,力争建立自己的政权。这就与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不同,他们则取旧政权而代之。可见,中国工商业者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先天的软弱性,多少世纪以来,始终只能做现存政权的附庸。关于这一论点,王教授在随后撰写的另一篇论文中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发挥,并点出:秦皇、汉武建立的专制封建王朝所推行的国家垄断经济体制,更加压制了民间工商业的活动空间(《从〈史记·货殖列传〉来推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阶段》,撰于1979年,1981年3月刊登在香港《抖擞》双月刊43期)。王毓瑚教授对《史记·货殖列传》的研究与评论,集中体现了他的独到的历史观。
王毓瑚教授还是一位历史地理学家,他在好几篇论文中都涉及到经济地理问题,包括前文介绍的《读〈史记·货殖列传〉杂识》在内。我认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当首推所著《我国历史上农耕区的向北扩展》,这是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脱稿于1977年。以下作一简要介绍。
这篇长文描述了从春秋战国以来几次较具规模的农耕区北移的过程,其中规模大而又影响深远的是清朝初年开始的大规模移民。这一轮农耕区北移的动因,主要是:在结束了蒙古、汉、满三族频繁的战争之后,内地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粮食需求越来越大。而在小农经济制度下,受技术停滞的制约,生产效率很难进一步提高。为求生存,内地农民迫切要求移垦。汉人北移几乎历来都是他们谋求新生活的老路。而东北地区和内古蒙地区虽然早有农耕,却只是星星点点,还有大片荒地,特别是满人进关后,东北地区更是地广人稀,急待开发。在这种形势下,虽然清朝初年政府采取了保护满族发源之地的政策,禁止汉人移垦,但是这个政策在移民洪流浪潮中,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山东人蜂拥渡海北进,先后开发了辽河流域和松花江流域大平原,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农业区。这段耕区北移的经历,体现了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威力。农耕区向蒙古牧区的移动,也受到清政府的阻挠,满人主要是防止蒙古、汉结合,危及清朝统治。但是,后来农业还是逐渐扩展到了牧区较为适合农耕的地区,并得到不断发展。王毓瑚教授对农耕移人牧区还有两点评论:第一,游牧业逐水草而居,不断流动,只是使用自然资源,却不保护和培养自然资源,这种生产方式,带有掠夺性质。而农耕则不同,利用自然资源,同时也保护和培养自然资源。所以,从牧业转变为农耕可看作生产力的一次飞跃.第二个论点是,在牧区滥垦,破坏了生态平衡,引起土地沙化,贻害无穷。
王教授对农耕区向北扩展过程的描述和评论告诉我们:经济地理的变动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虽然本质上它是经济活动的横向变化,却会涉及种族关系的融合或冲突、政府政策的取向、技术发展水平的高低等;而影响所及,既可能体现为生产力的飞跃,同时又可能遗患无穷。王教授这篇论文所体现的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与作为现代经济学一个分支的区位理论有许多相通之处。
在学习王毓瑚教授所著论文过程中,我深切感到,他的治学精神可谓气度恢弘,学术造诣博大精深,他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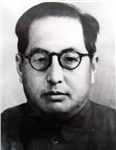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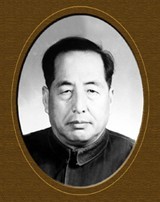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