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纽约的悼念
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吉林日报社下属的城市晚报。那一年长春的报界在这个小城市掀起了轩然大波。我刚刚上班就当上了头版和16版两个彩版的责任编辑,每周三和周六出版。奔忙的节奏和初入世事的尴尬,让我这个艺术生疲于奔命。那时候对周遭的世界并不敏感,对报社那懵懂的印象,就如同我们那座日伪时期的报社大楼,坚硬而刻板,深沉而压抑。我只是在想,这个大楼里得埋没了多少人的青春?沉积过多少匆匆的脚印?又有多少不该忘记却又总被忘记的故事?我在一个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喉舌媒体,在一个知识分子明争暗斗的利益场所,将会展开我怎样的一生?我总是会害怕的想起,有一天我也在这个位置上如同那个一身中草药味道的老编辑,上楼梯时托着千斤重腿,或者有一天我也如同那个编辑,为了分房子抢利益与朝夕相处或者某个素昧平生的人破口大骂。或者有一天我混到了平步青云,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说着自己不喜欢的话,照镜子看着不认识的自己。这些都是那么可怕的如影随形,于是好多奔放的不羁的年少轻狂,让我不由得不收敛,也不由得不略显沉重,虽然我外表平和,工作努力但是内心却总怀不甘。
于是就在工作一年后的那夜,在千禧年未到的那个晚上,发生了我和杨大哥的那些对话。我们说着那个最原始的话题:理想。也许在新年之际展望未来,本不足为奇,但是在压抑刻板的工作环境下有人与你摆脱于尘世的淤泥去壮志凌云,就显得极其可贵。12年过去了,我拼命的也想不起我们谈话的内容与细节,但是那个印象却深深留给了我,一个内心清高的学子风采,一个在89年,那个敏感岁月毕业的北大学生,多少还保存着对民主的渴望,与冷静理性的人生态度。这个印象使这个人物在我的心目中沉淀了一下,也视作在那个工作环境下少有的知己。我所喜欢的人从来不是位高权重,趋炎附势的功利人,从来不是蝇营狗苟,利害得失的市井人,我所喜欢的一定是那种灵魂清雅,不啻随波逐流的高贵人。
报社的计算机房,是我们电脑排版制版的地方。我们编辑去那里和工作人员排版,当时有个特别变态的规定,进屋要脱鞋,说是为了保护计算机。这个规定现在看起来是多么荒诞。但是偏有一个意气风发的老大妈就是坐在门口看着,谁不换鞋就扯开嗓门大喊。我们这些编辑每天很繁忙的穿梭在这里,再加上冬天东北人穿得本来就厚重,多有不便。于是就总有编辑趁着老大妈不注意就溜了了进来,能偷懒就偷懒。有一次,我们几个编辑没有换鞋在微机室工作。被老大妈发现了,这次她没有歇斯底里,虽然说话还是那么大声,“你们几个不换鞋是轻巧了,但领导得批评我。”这时候我的心理觉得一沉,好像做得很亏心的事情。同时我听到身后另外一个声音,“这么说我真是良心不安。”我循声望去,正是杨光。心理也不由得对他有了几分敬重。敬重他内心那种不加修饰的善良,也许以后没有多少人会知道我的改变,但那以后我每次去微机房,无论有人没人,从来都是主动换鞋的。也许这只是一个平凡的小事,但是却让我越来越习惯于体会别人的不易。也同时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而让我看到不足的恰恰是杨光。我所敬重的人一向不是盛气凌人的才子佳人,一向不是口若悬河的某某大牌,我敬重的一定是道德高尚,平易近人,体恤弱小的善良人。
之后每每在加班至深夜的时候,我们去宵夜,后来又有了城晚推出明星记者这一活动,杨光,左道,大雄,张颖,任三,被评为五个明星记者,我们的来往也更加频繁起来。杨光谦和,很有大哥的风范。对我总是有一种羡慕的感觉,还说他的女儿多么喜欢我的画。我其实也很关心他,总觉得他这样没日没夜的长期加班,不值得,为了谁呢?所以我们的话题往往都是逡巡于看破与执着之间。现在想来,杨大哥,你觉得小弟说得对么?你一定一如当年,是呀,你说的对!生命本该逍遥。灵魂本来就是应该自由的。但是你放不下你的责任。那无形又有形,那看似沉重又轻若蝉翼的责任。可是面对你的逝去,我也在反思,人活着最重要的有时候并不是自由的潇洒。而是所成就的功德。我不愿意用“事业”这个词,因为现在人把这个词理解得太过浅白。你在你的岗位上度过了一个无奈而劳苦的一生,可是你也在这个位置上尽你的所能为了内心的真诚和善良守护了一生。
后来我在中国千山万水,仿佛是自由,其实同样是劳累。同样在内心的囚笼。巴黎之后,我回长春,我没有举行婚礼,只邀请了四个同事,这其中就有你。我们相望而又相依的人生又是一程。现在我在美国,一样是各个城市的游走,此刻窗外是静静的哈德逊河,今天中午,当奎龙说你离去的消息,我正在纽约准备参加另一个媒体的活动。觥筹交错中没人体会到的我的伤感。曼哈顿上城拥挤的人流中也有一分为你的寂寞。
佛家用缘起缘灭来解释这世间的聚散,我也不认为死亡有多么可怕,他只是另外一种的生命形态。所以我并不觉得难过,我只是有所惋惜,惋惜有很多我应该说的话没有说得那么明了,也许在人生的某个岔路口我们的一次邂逅,会使未来的很多事情发生改变,一如12年前的那个夜晚,所以就要我们这些生者珍惜当下 ……
郭竞雄 于纽约曼哈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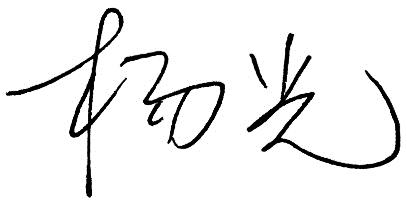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