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鼎初二作文《那年阳台》,发表于宜昌外校校刊《紫燕》2011年6月第一期
那 年 阳 台
陈文鼎
在我的记忆中,有那么一个阳台,它并不像许多童话里描绘的那样高贵、华丽,它只是一个普通男生寝室里毫不起眼、甚至有点脏的阳台。但是,在那阳台上,却埋藏着我的回忆,一个十四岁少年时而快乐、时而忧愁的回忆。
——题记
第一次来到那个阳台,是在期末考试前那次换寝室的时候。当时,阳台是那么平常,和其它寝室一样平滑的地面,一样洁白的瓷砖,一样透出点点锈迹的铁架,唯一不同的是,一抬头,就可以看见上一届住在这里的同学“留”给我们的、不知挂了多久的衣物。于是,经过我们寝室八人的合力整修,这阳台彻底变了样,变得与众不同:白瓷砖上堆满了我们的牙膏、牙刷,铁架上也挂满了五彩缤纷、形式各异的毛巾、抹布,头顶上的那些衣服,也通通被丢进垃圾箱。就这样,这个阳台,开始一点点、一点点融入我的生活。
每天清晨,阳台这里最为热闹。寝室里八个人,虽然每天早上坚持洗脸刷牙的只有那么三、四个,但这狭小的空间,还是显得有几分拥挤。因为地处江南水乡,早晨的窗外,总是笼罩着一层朦胧的薄雾,在雾中,窗外的一切显得那么虚幻,红白相间的操场,两旁种满各色植物的小路,冰冷的教学楼,以及尚未完全苏醒的大山,组成了一幅海市蜃楼般的画面。此时,若是来点小雨就更奇妙了,乍一看根本看不见的雨滴,一边抚摸着灌木丛与泥土,一边碰撞着楼房里的钢筋水泥,这些冗杂的声音仿佛直接从天上传来。早晨的阳台也最为繁忙,因为,我们马上就得端坐在那一间间排列整齐的教室里,大声诵读英语单词与文言古诗词了!
一个上午的学习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吃过午饭,回到寝室。这时的阳台较为宁静,而窗外却是一番热闹祥和的景象:穿着运动服的同学们正奔驰在操场上,颇为惬意的同学则慢悠悠地行走在小路上,还有一些勤奋的同学则趴在教室的课桌上。随着午休的铃声穿过整个寝室,窗外才逐渐静下来,操场上的同学们放慢了脚步,小路上的行人逐渐变得稀少,穿梭在各个寝室之间的同学们,也分成了两拨,一拨飞快地跑向教室,一拨则不慌不忙地回到了自己的寝室。我的室友大都比较勤奋,中午通常只有三四个同学在寝室休息。不知不觉中,中午的时间,就在我们的静默中流过。
转眼到了下午,下午的阳台刚开始较为安静,随着学校广播里传出悠扬的乐声,同学们开始陆续回到各自的寝室。在这个时间段,某些寝室的阳台,总有那么一些人,悄悄进行着鲜为人知的活动。我们的寝室就是这样,每到下午,这里的人渐渐增多,这些人聚集在阳台上,进行着只属于我们的游戏。在如此沉重的学习压力下,我们不顾一切,抓紧时间玩,抓紧时间娱乐,也许,这只是我们遗忘这个世界的方法罢了。当然,向晚的窗外,也别有一番韵味,落日懒洋洋地躺在群山之中,无力地释放着微弱的橙光,这光,均匀地铺在操场上,敏捷地穿梭在绿叶之中,同时也给那肃穆的高楼、坚硬的大山,镀上了一层淡黄色的金边。远处的都市,亮起点点灯光,在这灯光背后,无边的黑暗,正悄无声息地吞噬着天地间的一切。
等到晚自习结束,天已经彻底黑了,同学们回到寝室,草草地洗脸刷牙之后便躺到了床上。熄灯铃像是最终的审判,它的来临让整个寝室陷入一片黑暗,而窗外那皎洁的月光,就像一只只小精灵,趁机溜到了各寝室的阳台上,带来些许光亮。有时的夜晚,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眠,便起身来到阳台上,披着一身如水般冰冷的月光,通过这小小的窗口,眺望远方。此时的窗外,既静谧又喧闹:操场、教学楼以及大山,都死死地睡了过去,而远处的城市,则亮起了七彩的霓虹灯。站在这阳台上看那些光,感觉格外孤单,就像独自行走在一片黑暗之中,远处的光分明就是出口,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到达。窗外的风,是声音的使者,它带着整个世界的声音,涌向这里,涌向每个角落。我听见,风中,有人谈笑,有人哭泣,有人怒吼,还有人和我一样,伏在窗台上,眺望远方。有时,一道白色的裂痕突然出现在天空中,把黑暗一分为二,继而传来一阵低沉的滚雷声,这声音,好像是在咆哮,又好像是在哀号。于是,我的幻想被击碎,风依旧呼啸,只是那些奇幻的声音,都纷纷散去了。我无奈地回到了牢笼般的寝室,那些被锁闭在这里的人们,依然躲在被窝里,听着歌,看着小说,而我,却仿佛突然与这个世界隔绝,在我的世界里,只有我、风和月光。
阳台依旧是那个阳台,而我的记忆,却一点点地埋藏在这里。也许哪一天,当我重新翻开这尘封已久的回忆时,会突然发现:我,已不再是从前的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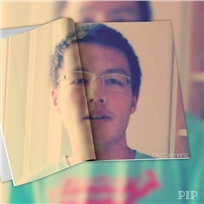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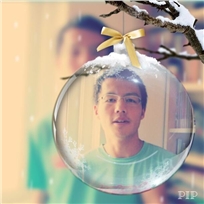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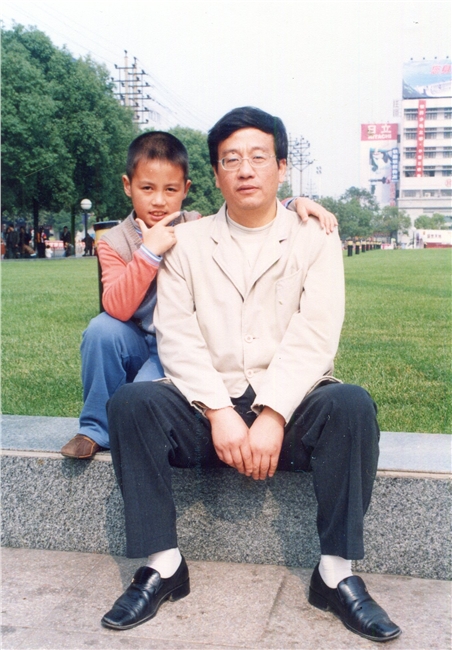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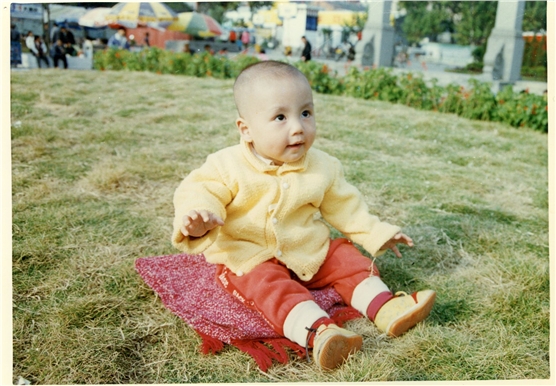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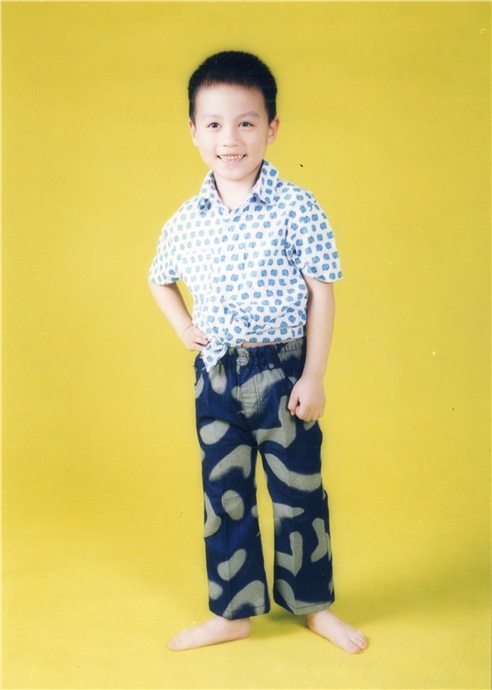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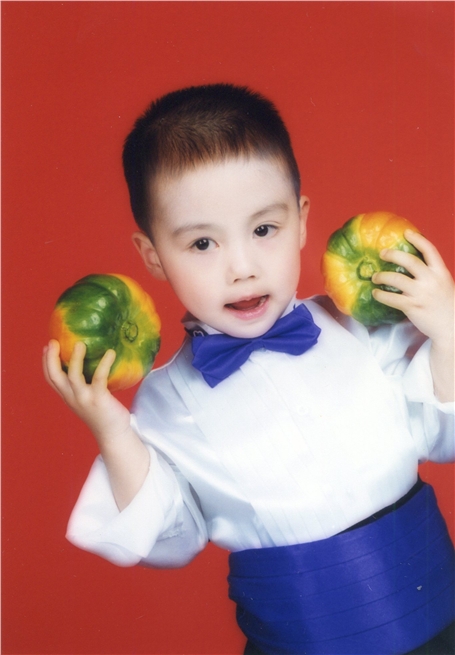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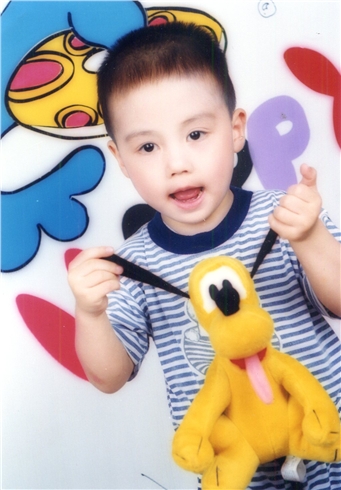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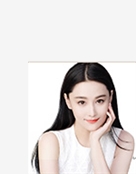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