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竹皮河
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三个清明,把这篇追忆散文献给父亲,再现他36岁时一个普通的生活场景。
1972年的仲夏,太阳透过房前老杨树的密密层层的叶子,把阳光的圆影照射在地上,知了在树上吱吱叫个不停。在爸爸开垦的小菜地里,才盛开的辣椒花,也皱卷起小花瓣,萎缩在蔫蔫叶子下。黑风口大桥下、竹皮河旁边的“干打垒”席棚房顶早已被骄阳烤的滚热了。
中午吃完饭,“干打垒”席棚房热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爸爸只穿短裤,也没穿鞋,就提着桶对我说:到竹皮河摸鱼、纳凉去。我高兴得屁颠屁颠学着爸爸的模样穿着短裤、光着脚走在后面。那天,在“十八团”小学读二年级的我正好放假,在清澈的河水里嬉戏,正是我所想的。
竹皮河发源于荆山山脉,属汉江小支流,是荆门市中心城区内唯一的一条自然河流。据《荆门州志》记载,竹皮河古时称“权水”,绕城区段称“蒙水”(古时象山称蒙山),下游称竹陂河,后来才演变成“竹皮河”。其源头有两支,北支出自城区西北郊圣境山东麓,流入城区浏河;西支出自城区西郊罗汉山麓,经海会沟,汇象山东麓蒙、龙、惠、泉四泉水,绕大、小南门流至北门桥,与浏河水汇为正流向东南流去,经钟祥天鹅院注入汉江,全长约50公里,流域面积473平方公里。传说竹皮河的上游以前种满竹子,荆门城内的居民要用竹子做竹器,就到上游去砍伐,将竹子放入河中漂流而下,城内的人再将竹子取走,竹皮河由此得名。
上世纪70年代初的竹皮河,河水清澈见底,鱼虾成群,竹林倒影掩映其中,绿波盈盈。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刘义忠先生所著《竹皮河记》是这样描述它的:“修竹郁郁葱葱,碧水汩汩悠悠,合城尽染”。《竹皮河记》镌刻在浏河岛上一块石碑上以说明竹皮河的历史和文化。
没走多远,下了一个坎就是河啦!河水清清的,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沾满了青苔滑滑的,翠绿翠绿的水草在河水的轻扶下悠悠荡荡。河两岸郁郁葱葱,杨柳随微微得河风轻轻地荡漾,挺拔的小叶杨也翻弄的叶子在河湾处平静的水面形成如墨倒影。在河的对岸三只白鸭在一只青灰色鸭子的带领下整逆水而上,时不时地挺起胸,哗哗煽动翅膀,发出嘎嘎叫声。
在河里嬉戏、纳凉的大人、小孩很多。河的两岸,现在的工建公司区域,当年驻扎着十七团全部和十八团、十六团部分建设大军和他们的家属。爸爸所属的十八团十二连从东宝水库旁迁移到黑风口大桥旁,竹皮河东岸居住。每当酷暑来临,深浅交错的竹皮河不仅是两岸建设大军消暑纳凉的好地方,也是他们洗净一身疲惫的天然浴场。
爸爸跟一个叔叔打了个招呼就踏进水里,走向河中心。我在河岸用小脚试试水,河水很凉,碰到水的一霎那,浑身战栗。犹豫间,爸爸回头望了我一眼,我这才鼓起勇气,跳进水里。爸爸向下游走去,边走边伏下身在石头边、在水草里摸着。我,学者其他小朋友的样,把手撑在河里小鹅卵石上,让清凉的河水没过我的脊背,仰着小脑袋,在水中爬行。爬了一小段,爸爸大声警告我“不要到前面来啦”我站起来一望,前面的河水已没到爸爸的腰部,我静静地站在河里。不一会,爸爸双手抓住一条鱼举过头顶,高兴地向往喊着“抓住一条、抓住一条”我惊喜得拔腿就向前跑,脚下一滑,“扑通”地一声,我又结实栽进河里,还咕噜地喝了一口水。
清澈的竹皮河,给我的童年带来无尽得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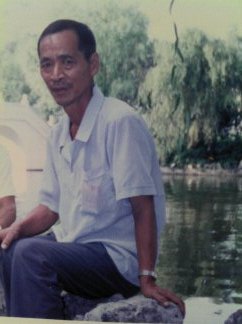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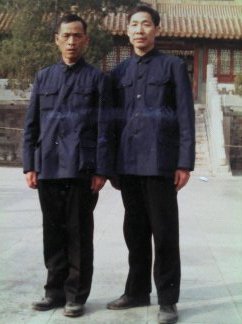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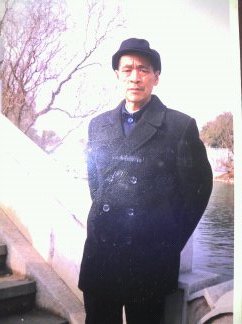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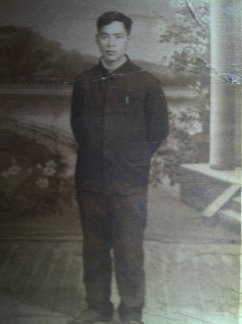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