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城里的那个热血青年
1931年秋,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携带这一个破旧的衣服挎包还有一件简单的行李。风尘仆仆从山西来到距北京不远的通州。走进了当时 的潞河中学。他带着山西汾阳教会的美国庚子赔款助学手续,他很自信,也很谦恭。
他从山西走来,从山西中阳县的一个山村走来,从一个四周大山的窑洞走来。
在20 年代的晋中地区的中阳县,一个叫做“师庄”的小山村的一家,九口人,父母和七个孩子。这个村子名叫“师庄”,全村却没有一个有文化的人。几十户人家散落在稀疏的几排窑洞中。这家几乎是村里最穷困的一家。没有一亩田。只靠租种别家的地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这两年几乎混不下去了。由于总是天旱,收成不好,缴了租子就所剩无几。无奈之下,父亲就携带全家搬进离村子十多里的大山里,村子里人叫那个地方“庄背”,一道沟坎面朝东南,挖开一孔窑洞就成了新家。那时候,深山里似乎是无主山地,穷苦人在那些地方开荒也没有别人干涉。
七个孩子最大的才十三岁。他每天扛着镐头跟在父亲的背后,刨开山坡上的土地,把荒草堆在一起点燃,就是肥料。每天弓着腰,一件看不出什么颜色的布衫总是透出酸臭的汗味。真正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一日复一日,没有除家里之外的人。他感到窒息,觉得自己快要变成哑巴了,觉得自己快要变成傻子了。他不甘心这样日复一日的混下去。看着四周的黄色的山,黄色的土地,还有父亲母亲那黄色的脸庞,他想走出去,他想走出大山。去寻找自己并没有目的的生活。他心中想,只要离开这大山,就一定会比现在好!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父亲劳作一天已经熟睡在窑洞里。他和妈妈暗地里商定。他要外出去闯世界。妈妈自然舍不得这个最大的孩子。可是,这个家会有出头之日吗?何况下面还有六个等饭吃、等衣穿的孩子。妈妈看得出大儿子是个有志向的孩子。也不愿意儿子就这样一辈子。她偷偷在儿子的衣兜里放了两块大洋,捡了两件旧衣裳。趁着夜色,瞒着父亲送儿子走出庄背,走出师庄,走出大山,去哪里,他不知道!他只想离开这让人窒息的大山。他认准只要离开大山,就会有出路!
走出大山的孩子,马上就沦为乞丐,他光着两只脚,在桑枣坡一代流浪了几十天。饿了就向人家讨饭吃,夜里随便找个地方安身。一天他发现自己来到了汾阳城。汾阳城距离他家不太远,只有一百多里,这里却完全是个开阔的小平原。汾阳城历史悠久,商业发达。人口集聚。交通也很方便。
这天,在一户人家的门洞里,人们发现了一个小男孩。人们看见这个小男孩子的时候,小男孩瑟缩索着身子,头发长长的。脸上很脏,一身单薄的土布外衣,扣子掉了几个,露着指头的一双土布鞋早已破乱不堪,与赤脚没什么两样。可是那一双大眼却清澈明亮,好多人看着这个孩子都在叹气:“唉!这年头啊!”
这时。一位中年妇女回头看见另一位女人走过来,说道:“唉!田太太,你来看,这个小孩子,真让人心疼!”
那位被称作“田太太”的女人走过来,拨开人群,用手帕给孩子擦了擦脸,问:“你是哪里人?怎么到这儿来啦?”
孩子睁着大眼睛,没有回答。只是用眼扫望眼前的人群。脸上没有胆怯,似乎并不在乎别人的议论。
田太太仔细端视着那个孩子,衣服很破烂,但并不显邋遢。脸上很憔悴,但却不灰暗。像是一个逃荒的,却没有任何奴相。眼睛里闪现出一种清新、自信、不卑的神情。田太太心里不由产生一种爱怜。她不再问那孩子话,却用手拍着孩子的肩说:“饿了吧,别怕。跟我来!”说着拉起孩子的手,让孩子跟她走。
那孩子也不胆怯,站起身,拍拍身上的土,跟在田太太的后面走了。
田太太是汾阳城里一家富户太太,自己姓贾,丈夫是汾阳城里教会的牧师。田太太把那孩子领回到自己家里,太太自身那种和气、温柔、亲切的女人气息,让孩子感到一种似乎像母亲一样的温暖。让人不自觉的没有了怯意。田太太让孩子在家里洗了澡,换上一身不太合身的衣服,并亲自下厨给孩子做了一碗阳春面。孩子吃的津津有味。
也许这个孩子长到十三岁,还不曾吃过这么香甜的阳春面,也许长到十三岁,也不曾体验过一个女人温柔的体贴。妈妈也关心他,也爱他。但那是黄土高原窑洞里粗糙的爱,远没有眼前这个女人这般细腻、这般温柔。也许他并不懂的这其中的区别在哪里。只是,他感到这是他冥冥之中,朦朦胧胧的向往。
饭后,田太太把孩子叫到身前,没等说话,那孩子却站在田太太面前,规规矩矩的给太太深深鞠了一躬。
田太太刚想问的话,却被孩子那一躬挡了回去,眼泪不禁流了出来。一把把孩子搂在怀里。泪水洒在孩子的头上。
孩子主动告诉田太太,自己姓张。家在中阳县师庄,今年十三岁,家里有七个孩子,自己是老大,因为家穷,父亲在山沟里开荒种地。又逢天旱,没有收成。父亲找了几个穷汉想合伙开煤窑挖点煤。没想到煤窑塌了砸死了几个人。官府把父亲抓了去。一个穷到底的人也不在乎吃官司。一条穷命也不值多少钱,正所谓“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死了人的苦主们在那年月也没有索赔的概念,自认倒霉罢了。不久官府就把父亲放了出来。在自己家里,四周都是荒山,一空破窑洞里一群饥寒交迫的孩子,实在没法过下去,就跟妈妈商量想外出闯世界,妈妈瞒着父亲,趁着黑夜,把孩子送出了家门。他四处流浪讨饭,到汾阳已经三个多月了。昨天走到汾阳城就溜到那家门洞里过夜。
田太太听着孩子的诉说,眼泪再一次夺眶而出:苦命的孩子,太太叹了口气说:“孩子,别走了,就留在这里吧!”
那天,田太太的丈夫田牧师回到家里,太太跟丈夫讲了孩子的身世。然后把孩子推到丈夫面前说:“这孩子我留下了,你想办法给孩子找个差事吧!”田牧师看这孩子眉清目秀,规规矩矩,心里也很喜欢,自家没有孩子,太太又那样执意留下。也就不再说什么。
田牧师原名田树棠,汾阳城里人。自从汾阳城有了基督教会后,就入了教。原来教会是美国人办的,后来美国人把教会交给了田树棠主持,
这个孩子好像也与田家有一种缘分,自打留在田家,孩子勤勤快快,帮田太太收拾家务,打扫卫生,劈柴洗衣。太太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就经常教孩子识字,孩子说在家上过私塾。认识许多字,田太太很高兴,就拿出新的识字课本教孩子学习,不仅有国语,还有数学,田太太还会英文。于是,田太太就在家里教孩子读书。补习数学和英文。
田家在汾阳交际很多,和许多富户都有往来。许多富家都知道田牧师收留了一个孩子。经常让田太太带着孩子去家串门。富家婆看见这个孩子都很喜爱这个孩子。好多家都想收留他,田太太自然不答应。就这样,孩子在田家过了两年。
几年后,田太太提议让孩子到学校去读书。田牧师为这孩子办理了庚子赔款助学款手续,把孩子介绍到汾阳铭义教会中学。在田家太太补习功课有了基础,学习成绩不错。孩子还是拿田家当自己的家,经常回家帮太太做些家务。这个孩子在汾阳初中学业期满,毕业成绩优秀。田家想让孩子继续高中学习,但是汾阳没有高中班。去外地只能去北京附近的通州潞河中学。去那里则必须办理另一笔庚子赔款助学手续。这手续一时办不下来。只好暂时休学。这一段时光,曾回过中阳县老家看望父母并在村里教书。还曾去陕西府谷县教书。又过了几年。汾阳田家终于从教会办到了庚子赔款助学款。于是,他匆匆离开陕西府谷,踏上了去北京通州潞河中学的求学之路。 这一年是1931年秋。
这个青年就是我的父亲张丕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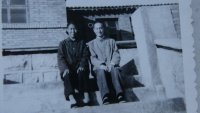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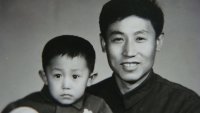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