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父亲日记所感
这些天,整理老爸的日记。我慢慢知道,老爸小时候是很有志向的,他不甘心在师庄那个小村子,像爷爷那样“背朝黄土面朝天”的过一辈子。这也许是因为他是爷爷的长子,受到了宠爱,所以能够上六年私塾。因此,心里有了“不甘”的意念。所以,爷爷带着二叔去庄背开荒,却把父亲留在师庄继续读书。那时就有“郑二孩”喜欢父亲,想和父亲结成一家。
那年,因为天旱无雨,庄背过不下去了。奶奶回到娘家,爷爷带着二叔、三叔迁移找有有水的地方度日。爸爸就跑出来,先在桑枣坡,在那里,就有人喜欢他。爸爸也非常勤谨,被颜老先生介绍到汾阳教会当学徒。
在汾阳,田太太十分喜爱父亲,那时的田太太不过24岁。她把父亲视为亲弟弟。百方照料。杨老先生一家也看上了父亲。父亲上学是杨老先生的功劳。杨家三女儿似乎想招父亲作婿。所以着意培养父亲入学。
在通州潞河中学,父亲不仅得到王乃堂的青睐,而且受到万博士的友谊。父亲那时正值“风华正茂,挥斥方遒”。广交朋友、四处活动,尽做善事。深得人心。因此,又到北京肖村“乡村改造实验室”工作。如果不是卢沟桥事变。父亲在那里肯定会大有作为的。
父亲是幸运的,因此他获得了那么多人的帮助,这种帮助改变了他出生在山村的命运。这当然与他的努力分不开。
父亲又是不幸的,因为家境贫寒。虽然上完高中,但没能进一步上大学或是出国深造。王乃堂其实也没有大学文凭。王乃堂是抗战后的经历,走上了以后的路。
我常想:父亲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总能顺风顺水的进步。而到了解放后,进了干校后,反而逆水行船了,屡屡受挫呢?
我觉得,解放前的时代,社会上的道德观念、人际关系、是非观念要比解放后简单得多,清亮得多,“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自然而然的通行。不像解放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你整我,我整你。人们弄不明白到底怎样才是“好人”。在这种氛围里,人们小心翼翼,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不知那块天上飞来之石,会砸在自己头上。
因此,在这种环境里,好人未必会有好下场,坏人未必受人谴责。需要你学会钻营、学会阿谀、学会察言观色,学会明哲保身。如果你不会这些本领,你就注定不会有好下场!
这样的社会,人们的精力都用在了不正经的地方了。那些社会精英,都没精力去在自己领域潜心钻研,也没心思去做善事。而这些人又鄙视这种让人讨厌的世俗哲学。所以,整个社会就不会造成诚信的环境。体现在教育方针、教育方法、教育方向、教育成果上的,就是“钱学森之问”所要回答的问题。
余秋雨曾对这种环境做过评价:我们的历史太长,权谋太深,兵法太多,黑箱太大,内幕太厚,口舌太贪,眼光太杂,预计太险。因此,对一切都构思过度。
这种环境,往往都是思谋极深的人能够得势。他们周围总能聚集一大圈阿谀奉承的小人。而小人治国,不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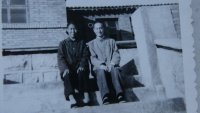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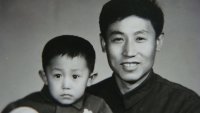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