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从中午开始(2)
说实话,对我国当代文学批评至今我仍然感动失望。我们常常看到,只要一个风潮到
来,一大群批评家都拥挤着争先恐后顺风而跑。听不到抗争和辩认的声音。看不见反叛者。而当另一种风潮到来的时候,便会看见这群人作直角式的大转弯,折过头又向相反的方向涌去了。这可悲的现象引导和诱惑了创作的朝秦暮楚。同时,中国文学界经久不衰且时有发展的山头主义又加骤了问题的严重性。直言不讳地说,这种或左或右的文学风潮所产生的某些“著名理论”或“著名作品”其实名不副实,很难令人信服。
在中国这种一贯的文学环境中,独立的文学品格自然要经受重大考验。在非甲必乙的格局中,你偏是丙或丁,你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之所以还能够坚持,是因为你的写作干脆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系。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
那么,在当前各种文学思潮文派日新月异风起云涌的背景下,是否还能用类似《人生》式的已被宣布为过时的创作手法完成这样作品呢?而想想看,这部作品将费时多年,那时说不定我国文学形式已进入“火箭时代”,你却还用一辆本世纪以前的旧车运行,那大概是十分滑稽的。
但理知却清醒地提出警告:不能轻易地被一种文学风潮席卷而去。实际上,我并不排斥现代派作品。我十分留心阅读和思考现实主义以外的各种流派。其间许多大师的作品我十分崇敬。我的精神常如火如荼地沉浸于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开始直至欧美及伟大的拉丁美洲当代文学之中,他们都极其深刻地影响了我。当然,我承认,眼下,也许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斯汤达,曹雪芹等现实主义大师对我的影响要更深一些。我要表明的是,我当时并非不可以用不同于《人生》式的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部作品,而是我对这些问题和许多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就我个人的感觉,当时我国出现的为数并不是很多的新潮流作品,大都处于直接借鉴甚至刻意模仿西方现代派作品的水平,显然谈不到成熟,更谈不到标新立异。当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这些作品的出现本身意义十分重大,这是毋容置疑的。我不同意那些感情用事的人对这类作品的不负责任的攻击。从中国和世界文学史的角度观察,文学形式的变革和人类生活自身的变革一样,是经常的,不可避免的。即使某些实验的失败,也无可非议。
问题在于文艺理论界批评界过分夸大了当时中国此类作品的实际成绩,进而走向极端,开始贬低甚至排斥其它文学表现样式。从宏观的思想角度检讨这种病态现象,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和不久前"四人帮"的文艺特殊同归,必然会造成一种新的萧瑟。从读者已渐渐开始淡漠甚至远离这些高深理论和玄奥作品的态度,就应该引起我们郑重思考。
在我看来,任何一种新文学流派和样式的产生,根本不可能脱离特定的人文历史和社会环境。为什么一路新文学现象只在某一历史阶段的某个民族或语种发生,此如当代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为什么产生于拉美而不是欧亚就能说明问题。一种新文学现象的发生绝非想当然的产物。真正的文学新现象就是一种创造。当然可以在借鉴的基础上创造,但不是照猫画虎式的临幕和改头换面的般弄,否则,就很可能是'南橘北移"。因此,对我国刚刚兴起的新文沉思潮,理论批评首行有责任分清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模仿甚至是变相照抄,然后才可能估价其真正的成绩。当我们以为是一颗原子弹问世的时候,其实许多年前早就存在于世了;甚至几百年前中国的古人已经做得比我们还好;那么为此而发出的惊叹就太虚张声势了。一九八七年访问德国(西)的时候,我曾和一些国外的作家讨论到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并且取得了共识。我的观点是,只有在我们民族伟大历史文化的土壤上产生出真正具有我们自己特性的新文学成果,并让全世界感动耳目一新的时候,我们的现代表现形式的作品也许才会趋向成熟。正如拉丁美洲当代大师们所做的那样。他们当年也受欧美作家的影响(比如福克纳对马尔克斯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一直跟踪而行,反过来重新立足于本土的历史文化,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真正属于自己民族的创造性文学成果,从而才又赢得了欧美文学的尊敬。如果一味地模仿别人,崇尚别人,轻视甚至藐视自己民族传大深厚的历史文化,这种生吞活剥的"引进"注定没有前途。我们需要借鉴一切优秀的域外文学以更好地发展我们民族的新文学,但不必把"洋东西"变成吓唬我们自己的武器。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当代西方许多新的文化思潮,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和影响,甚至已经渗透到他们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而我们何以要数典忘祖轻溥自己呢?8至于当时所谓的"现实主义过时论",更值得商榷。也许现实主义可能有一天会"过时",但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代里,现实主义仍然会有蓬勃的生命力。生活和艺术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而不在于某种存在偏见的理论妄下断语。即使有一天现实主义真的"过时",更传大的"主义"君临我们的头顶,现实主义作为一定历史范畴的文学现象,它的辉煌也是永远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认真考察一下,现实主义在我国当代文学中是不是已经发展到类似十九世纪俄国和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在反映我国当代社会主生活乃至我们必须重新寻找新的前进途径?实际上,现实主义文学在那样伟大的程度,以致我们不间断的五千年文明史方面,都还没有令人十分信服的表现。虽然现实主义一直号称是我们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和新近兴起的现代主义一样处于发展阶段,根本没有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的地步。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决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而主要应该是一种精神。从这样的高度纵观我们的当代文学,就不难看出,许多用所谓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品,实际上和文学要求的现实主义精神大相径庭。几十年的作品我们不必一一指出,仅就“大跃进”前后乃至文革十年中的作品就足以说明问题。许多标榜“现实主义”的文学,实际上对现实生活作了根本性的歪曲。这种虚假的"现实主义"其实应该归属“荒诞派”文学,怎么可以说这就是现这主义文化呢?而这种假冒现实主义一直侵害着我们的文学,其根系至今仍未绝断。文革以后,具备现实主义品格的作品逐渐出现了一些,但根本谈不到总体意义上的成熟,更没有多少容量巨大的作品。尤其是初期一些轰动社会的作品,虽然力图真实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面貌,可是仍然存在简单化的倾向。比如,照旧把人分成好人坏人两类——只是将过去"四人帮"作品里的好坏人作了倒置。是的,好人坏人总算接近生活中的实际“标准”,但和真正现实主义要求对人和人与人关系的深刻揭示相去甚远。此外,考察一种文学现象是否"过时",目光应该投向读者大众。一般情况下,读者仍然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它有理由继续存在。当然,我国的读者层次比较复杂。这就更有必要以多种文学形式满足社会的需要,何况大多数读者群更容易接受这种文样式。“现代派”作品的读者群小,这在当前的中国是事实;这种文学样式应该存在和发展,这也毋容置疑;只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负责任地弃大多数读者于不顾,只满足少数人。更重要的是,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甚至可以满足各个层面的读者,而新潮作品至少在目前的中国还做不到这一点。至于一定要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现代派创作方法之间分出优劣高下,实际是一种批评的荒唐。从根本上说,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高水平的作品,也可能写出低下的作品。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创作,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艺术的平庸。一个成熟的作家永远不会“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他们用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杰出的篇章。当我反复阅读哥伦比亚当代伟大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著名的《百年孤独》的时候,紧接着便又读到了他用纯粹古典式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新作《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是对我们最好的启发。
以上所有的一切都回答了我在结构《平凡的世界》最初所遇到的难题——即用什么方式来构建这部作品。
我决定要用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部规模庞大的作品。当然,我要在前面大师门的伟大实践和我自己已有的那点微不足道的经验的基础上,力图有现代意义的表现——现实主义照样有广阔的革新前景。我已经认识到,对于这样一部费时数年,甚至可能耗尽我一生主要精力的作品,绝不能盲目而任性,如果这是一个小篇幅的作品,我不妨试看赶赶时髦,失败了往废纸篓里一扔了事。而这样一部以青春和生命作抵押的作品,是不能用"实险"的态度投入的,它必须在自己认为是较可靠的,能够把握的条件下进行。老实说,我不敢奢望这部作品的成功,但我也"失败不起"。这就是我之所以决定用现实主义方法结构这部作品的基本心理动机和另一个方面。
我同时意识到,这种冥顽而不识时务的态度,只能在中国当前的文学运动中陷入孤立境地。但我对此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孤立有时候不会让人变得软弱,甚至可以使人的精神更强大,更振奋。毫无疑问,这又是一次挑战。是个人向群体挑战。而这种挑战的意识实际上一直贯穿于我的整个创作活动中,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是这样,《在困难的日子里》也是这样。尤其是《人生》,完全是在一种十分清醒的状态下的挑战。
在大学里时,我除过在欧洲文学史,俄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指导下较系统地阅读中外各个历史时期的名著外,就是钻进阅览室,将中国建国以来的几乎全部重要文学杂志,从创刊号一直翻阅到文革开始后的终刊号,阅读完这些杂志,实际上也就等于检阅了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主要成就及其代表性作品。我印明很强烈的是,这些作品中的人很少例外地被分成好坏两种。而将这种印象交叉地和我同时阅读的中外名著作一比较,我便对我国当代文学这一现象感动非常的不满足,当然出就对自己当时的那些儿童涂鸦式的作品不满足了。'四人帮'时代结束后,尽管中国文学摆脱了禁锢,许多作品勇敢地揭示社会问题并在读者群众中引起巨大反响,但仍然没有对这一重要问题作根本性的检讨。因此,我想对整个这一文学现象作一次挑战性尝试,于是便有写《人生》这一作品的动机。我要给文学界,批评界,给习惯于看好人与坏人或大团圆故事的读者提供一个新的形象,一个急忙分不清是“好人坏人”的人,对于高加林这一形象后来在文学界和社会上所引起的广泛争论,我写作时就想到了—…这也正是我要达到的目的。
既然我一直不畏惧迎风而立,那么,我又将面对的孤立或者说将要进行的挑战,就应当视为正常,而不必患得患失,忧心忡忡。应该认识到,任可独立的创造性工作就是一种挑战,不仅对令人,也对古人,那么,在这一豪迈的进程中,就应该敢于建立起一种"无榜样"的意识——这和妄自尊大毫不相干。
“无榜样意识”正是建立在有许多榜样的前提下。也许每一代作家的使命就是超越前人(不管最后能否达到),但首先起码应该知道前人已经创造了多么伟大的结果。任何狂妄的文人,只要他站在图书馆的书架面前,置身于书的海洋之中,就知道自己有多么渺小和可笑。
对于作家来说,读书如同蚕吃桑叶,是一种自身的需要。蚕活到老吃到老,直至能口吐丝线织出茧来;作家也要活到老学到老,以使自己也能将吃下的桑叶变成茧。
在《平凡的世界》进入具体的准备工作后,首先是一个大量读书过程。有些书是重读,有些书是新读。有的细读,有的粗读。大部分是长篇小说,尤其是尽量阅读,研究,分析古今中外的长卷作品。其间我曾列了一个近百部的长篇小说阅读计划,后来完成了十之八九。同时也读其它杂书,理论,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和宗教著作等等。另外,还找一些专门著作,农业,商业,工业,科技以及大量搜罗许多知识性小册子,诸如养鱼,养蜂,施肥,税务,财务,气象,历法,造林,土壤改造,风俗,民俗,UFO(不明飞行物)等等。那时间,房子里到处都搁着书和资料,桌上,床头,茶几,窗台,甚至厕所,以便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随手都可以拿到读物。读书如果不是一种消遣,那是相当熬人的,就像长时间不间断地游泳,使人精疲力竭,有一种随时溺没的感觉。书读得越多,你就越感动眼前是数不清的崇山峻岭。在这些人类已建立起的宏传精神大厦面前,你只能“侧身西望长咨嗟!”在“咨嗟”之余,我开始试着把这些千姿百态的宏大建筑拆卸开来,努力从不同的角度体察大师们是如何巧费匠心把它们建造起来的。而且,不管是否有能力,我也敢勇气十足地对其中的某些著作“横挑鼻子竖挑眼”,去鉴赏它们的时候,也用我的审美眼光提出批判,包括对那些十分崇敬的作家。在这个时候,我基本上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我甚至有意“中止”了对眼前中国文学形势的关注,只知道出现了洪水一样的新名词,新概念,一片红火热闹景象。“文坛”开始对我淡漠了,我也对这个“坛”淡漠了。我只对自己要做的事充满宗教般的热情。“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只能如此。这也很好。
有我所有阅读的长篇长卷小说中,外国作品占了绝大部分。从现代小说意义来观察中国的古典长篇小说,在成就最高的《水浒》,《三国演义》,《金瓶梅》和《红楼梦》四部书中,《红楼梦》当然是峰巅,它可以和世界长篇小说史上任何大师的作品比美。在现当代中国的长扁小说中,除过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我比较重视柳青的《创业史》。他是我的同乡,而且在世时曾经直接教导过我。《创业史》虽有某些方面的局限性,但无疑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具有独特的位置。这次,我在中国的长卷作品中重点研读《红楼梦》和《创业史》。这是我第三次阅读《红楼梦》,第七次阅读《创业史》。
无论是汗流浃背的夏天,还是瑟瑟发抖的寒冬,白天黑夜泡在书中,精神状态完全成 一个准备高考的高中生,或者成了一个纯粹的“书呆子”。11为写《平凡的世界》而行的这次专门的读书活动进行到差不多甚至使人受不了的情况下,就立刻按计划转入另一项
“基础工程”——准备作品的背景材料。
根据初步设计,这部书的内容将涉及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
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期,其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历史性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这部企图用某种程序的编年史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们。当然,我不会用政治家的眼光审视这些历史事件。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性事件的态度;看似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哪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克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但是,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中立",他必须做出哲学判断(即使不准确),并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人性。正如传大的列夫·托尔斯泰所说:“在任何艺术作品中,作者对于生活所持的态度以及在作品中反映作者生活态度的种种描写,对于读者来说是至为重要,极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艺术作品的完整性不在于构思的统一,不在于对人物的雕琢,以及其它等等,而在于作者本人的明确和坚定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渗透整个作品。有时,作家甚至基本可以对形式不作加工润色,如果他的生活态度在作品中得到明确,鲜明,一贯的反映,那么作品的目的就达到了。"(契尔特科夫笔录,一八九四年)。
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应该完全掌握这十年间中国(甚至还有世界——因为中国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世界的一员)究竟发生过什么。不仅是宏观的了解,还应该有微观的了解。因为庞大的中国各地大有差异,当时的同一政策可能有各种做法和表现。这十年间间发生的事大体上我们都经历过,也一般地了解,但要进入作品的描绘就远远不够了。生活可以故事化,但历史不能编造,不能有半点似是而非的东西。只有彻底弄清了社会历史背景,才有可能在艺术中准确描绘这些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形态。
较为可靠的方式是查阅这十年间的报纸——逐日逐月逐年地查。报纸不仅记载于国内外第一天发生的重大事件,而且还有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性反映。
于是,我找来了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一种省报,一种地区报和《参考消息》的全部合计本。
房间里顿时堆起了一座又一座“山”。
我没明没黑开始了这件枯燥而必需的工作,一页一页翻看,并随手在笔记本上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的大事和一些认为"有用"的东西。工作量太巨大,中间几乎成了一种奴隶般的机械性劳动。眼角糊着眼屎,手指头被纸张靡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只好改用手的后掌(那里肉厚一些)继续翻阅。用了几个月时间,才把这件恼的人工作做完。以后证明,这件事十分重要,它给我的写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任何时候,我都能很快查找到某日某月世界,中国,一人省,一个地区(地区又直接反映了当时基层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什么。在查阅报纸的同时,我还想得到许多当时的文件和其它至关重要的材料(最初的结构中曾设计将一两个国家中枢领导人作为作品的重要人物)。我当然无法查阅国家一级甚至省一级的档案材料,只能在地区和县一级利用熟人关系抄录了一些有限的东西,在极大的遗憾中稍许得到一点补充,但迫使我基本上放弃了作为人物来描写国家中枢领导人的打算。
一年多的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但是,似乎离进入具体写作还很遥远。所有的文学活动和其它方面的社会活动都基本上不再参与,生活外于封闭状态。全国各地文学杂志的笔会时有邀请,一律婉言谢绝。对于一些笔会活动,即使没胡这部书的制约,我也并不热心。我基本上和外地的作家没有深交。一些半生不熟的人凑到一块,还得应酬,这是我所不善长的。我很佩服文艺界那些"见面熟"的人,似乎一见面就是老朋友。我做不到这一点。在别人抢着表演的场所,我宁愿做一个沉默的观众。
(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管理员 林娜整理
由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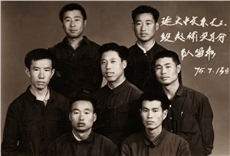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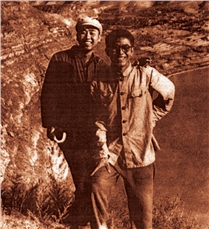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