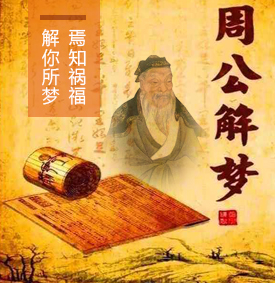“一生爱恋融哲思,普世乡愁化恩典” ——悼念恩师胡伟希教授
“一生爱恋融哲思,普世乡愁化恩典”,这是我的忘年交张化之老师为胡师所撰挽联中的两句。它巧妙地将老师的两部作品与他一生的志业绾合在一起。“哲思”取自他的《流年无语——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哲思》。确实,老师一生的绝大部分时期均在进行“智慧的探索”和“思想的冒险”。他浸润其中,常常有“沉醉不知归路”之感。“恩典”则出自他的另外一部著作——《生命的恩典:幸福与痛苦》。诚然,胡师更喜爱抽象的思辨,但是只要深入阅读他的作品,你就会发现他有着很强烈的生命关切和家国情怀。这是一股若隐若现的“乡愁”,但它并非单纯是一种怀旧式的追忆,更多是面向未来的远瞻。
一
胡师祖籍湖南长沙,1947年出生于湖北武汉,后因父亲工作的调动,举家迁徙至广东韶关。在那里,他度过了意气风发、无拘无束的青葱岁月。胡师自小就酷爱读书,手不释卷,几至废寝忘食。当地的各大图书馆,时不时地出现这位翩翩少年的身影。他的成绩一直很好,常常名列前茅,是班级乃至学校的骄傲。看到家里出了一个读书的好苗子,父母自然倾力支持他读书,甚至从不让他干家务。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当时韶关地区最好的中学——北江中学。在校期间,他不仅学业优秀,而且为人亲和、知识渊博、勤学深思,在同学当中有“卧龙”的美誉。1965年的高考,他的分数达到其心仪的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线。然而,在那一个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因为父亲曾经有过服役国民党部队的经历,他最后只能与清华擦肩而过。在二十年后,他选择去清华执教,或许也是出于弥补当初的遗憾吧!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977年恢复高考,华夏大地重新开启了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的时代新风,从而改变了许多读书人的命运。因为“文革”的耽误,囤积了十多年的中学生蜂拥而至,加入高考的大军。这一年,高考报名人数达到570万,录取仅27万,录取率不到5%。在这“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争态势之下,胡师依然凭着过硬的实力考取了广东工学院(广东工业大学的前身)的分析化学系。入学一年后,他即参加了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并顺利考取了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从王栻教授。1981年,他从南京大学毕业,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分配至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并担任《学术研究》杂志的编辑。1983年,胡师再次考取南京大学,入哲学系孙叔平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不料及门不久,孙教授却因心脏病猝发不幸离世。当时的文科博导较少,与他同门的赖永海教授转入任继愈先生门下受教,而他则改投冯契先生门下,最终于1986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有意思的是,他的研究生学历和博士学位证书分别是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授予的,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胡师的博士论文是围绕金岳霖先生展开的。金先生是中国逻辑学科的奠基人,也是冯契先生的老师,他是能够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一位学者,其作品佶屈聱牙,晦涩难懂。胡师由史学转入哲学,阅读师爷的作品自然难度不小。但是,他发扬“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精神,硬是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博士论文,极大地提升了他的哲学分析能力。毕业后,他先后出版了《金岳霖与中国实证主义认识论》《金岳霖哲学思想》两书,其中后者在1996年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胡师博士毕业后,决定去清华工作,很多人表示不解。因为当时他属于委托培养,南京大学要求他博士毕业之后回校任教,并承诺解决配偶安置问题。为什么要去清华呢?他说作为南方人已经去过了南方很多地方,但是北京从未去过,心下特别向往。在一次庐山举办的学术会议上,一位来自北京的学者对他说:“做学问,还是得到北京!”这句话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恰在此时,成立不久的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招人,当得悉这个工作并不需要上多少课,有大把的时间从事科研,这就更加坚定了他去清华工作的决心。当时的文科博士非常少,南京大学自然不愿意放人。我很难想象老师这样一位文质彬彬、温润如玉的读书人,为了跳槽如何能够与校方软磨硬泡三个月。结果,经过南大校长亲自批示“合情合理,酌予办理”,最终让胡师圆了自己的“清华梦”。
进入清华大学工作的前几年,生活过得异常清苦,居住条件局促而又简陋,曾不得不多次搬家。一位北大工作的朋友造访老师的斗室,大发感慨:“老胡,你活得太惨了!”好在他并没有把这话当回事,因为他更多关注自己精神世界的丰盈,可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直到20世纪初,清华南门的蓝旗营小区竣工,老师才有着自己的“安居”。最让他高兴的是,清华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工作为他亲近学界前辈提供了便利。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成了他的上级领导,知名学者何兆武、张岂之、钱逊等先生曾是他的同事。怀着对前辈学者的景仰,他不时地造访学术前辈与名家,向他们讨教与问学。老师说,他一生当中拜访了许多学界名人,与这些大学者的每一次接触,几乎都是自己灵魂的一次飞升。一方面有前辈学者的熏陶和提携,另一方面,贤惠的师母几乎承揽了全部的家务,老师全身心地投入了自己挚爱的学术事业,并且取得了累累的硕果。
2018年,我赴台湾的辅仁大学士林哲学研究中心访学,期间有缘拜会著名思想家韦政通先生。我问他是否认识胡老师,他说他和傅伟勋先生共同主持“世界哲学家丛书”,其中《张东荪》一书是他邀约胡师来撰写的,可是却被委婉地拒绝了。韦先生表示,他一直百思不得其解。那时候,大陆与台湾的经济差距比较大,该书的稿费又特别丰厚。很多大陆学者为了得到这样的机会,主动写信毛遂自荐,从未没有遇到推辞的情况。后来,我在与老师在电话中说起这件事。他说那一年手头同时在写三本书,若再写张东荪,可能会研究质量不高。他还说,人民出版社曾向他约稿写罗素,因为他之前写过两本罗素的书,所以他不愿意写了。因为他觉得写作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一次学习提升的过程,倘使写不出什么新东西,没有什么新想法,还不如不写的好。听完这番话,我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老师对学术的爱是一种纯洁的爱,是一种不容亵渎、不打折扣的爱,他之所以能够始终能够保持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心态,与这种纯洁的爱是完全分不开的。
二
在读硕士的时候,导师郑晓江教授推荐我报考胡老师的博士。在获得胡老师的联系方式之后,我向他介绍了我硕士论文做的是奥地利心理学家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学”。他对选题表示肯定,并勉励我好好准备考博的复习。怎奈那一年,我虽然笔试考取了第一,但是面试表现不佳。好在第二年,总算圆了我的清华梦。第一次见到老师,他的儒雅气质与君子风范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读博期间,我发电子邮件请他为我改文章。他在回信中,首先肯定我的文章有新意,然后话锋一转,又说,如果这样改,这篇文章就会更加完美。我很惊讶这种表达方式,让人感觉无比舒服。既保全了我的“面子”,也让我意识到了“问题”。至于博士论文选题,他说你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于是,我选择了荀子的思想展开研究。因为在我看来,荀子是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要弄通先秦思想,从荀子入手倒是不错的选择。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在整体架构的设计方面不太满意,但是却有几篇感觉还算有新意的文章。后来,那篇《“法、术、势”思想新探》的文章还应编辑的要求邀请老师写了两三百字的评语,对我而言也是一种鼓励。因为我读的是在职博士,虽然完全脱产,但是在三年内毕业也并非易事。在博士论文即将成稿之前,我在个人情感上遭遇了挫折,一度影响了写作的进度。直到2009年春节前夕,我才找到写作状态。当胡师获悉我春节不回家之后,他打电话邀我到他家吃年夜饭。我清晰地记得在胡师家热腾腾的饭桌前,我们一起闲聊的场景。毕业之后,他推荐我的博士论文在台湾花木兰出版社出版,并且写了一篇很长的书序。
毕业之后,我几乎一个月给他打一次电话。有时候聊学术,有时候聊生活。在生活方面,不论是面临人生抉择也好,还是遭遇人生逆境也好,老师总是给予我诚挚的勉励和耐心的开导。刚刚走上工作岗位那会,不免愤世嫉俗。尤其是感觉现在的中国学术圈课题和核心期刊完全绑架了学术,似乎也看不出学问不学问了。胡师提到冯友兰先生说过一句话:“哲学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很长一段时间他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当得知冯友兰先生90多岁在目力近盲的情况下,还在创作《中国哲学史新编》,这让他豁然有悟:思想者是靠著书立说来“立身”的,只有经得起时代和后人的检验,才真正谈得上是“立”住,而不会被后世所淘汰。至于如何真正“立”住,那就必须具备陈寅恪先生所讲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接着,他对我说,做学问是自己的事情,外在的职称也好,荣誉也好,名利也好,并不一定反映真实的学术能力。对于学者而言,后人但凡看过你的书或者文章,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你的学术水平了,如此而已。这番话可谓一针见血,至少让我明白自己真正应该追求什么。
当谈到学术时,一向理性的老师甚至有时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有一天晚上,我和胡师“话聊”了两个多小时。本来是给他谈科研经费报销的事情,结果聊到学术时,他的兴致完全收拾不住,滔滔不绝,完全没有我插话的余地。我想,倘使没有深入骨髓的挚爱,怎么会对哲学这种抽象的东西抱以如此的热情。胡师坦言他对目前中国哲学的研究状况并不满意。他认为当下的研究更多的还是思想史研究,很难称得上是哲学史研究。即使有哲学史研究,又很难称得上哲学的研究。他认为哲学史的工作,冯友兰算是做得很好了,但是后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仅是几个人所能解决的,甚至需要几代人的积累。他认为做学术,确实需要勤奋,但是也需要天赋。在他看来,做哲学的淘汰率要比文学和史学高多了。在聊研究方法的时候,他说早期一代接受西学系统训练的学者,大抵能够掌握一套学术研究方法,故而后来转入中国学术史研究能够得心应手。至于他本人,受益最大的是在研究金岳霖思想的时候,深入研究了西方的逻辑实在论。他还说,等过两年直接读英文原著,或可从西方的学术名著中汲取更多的创作灵感。退休之后,可能更能够集中自己的精力,好好地想清楚一些问题。在我阅读过殷海光先生一些作品后,我发现老师身上明显具有金岳霖一派(或者胡师所说的“清华学派”)特有的风格——追求自由思想、崇尚精神独立、注重逻辑分析、融贯古今中西。冯契先生有句传世名言:“不论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这是爱智者的本色。”胡师在怀念冯先生的文章“题记”中亦说:“选择了哲学意味着选择了人生——‘智慧’的人生。”
除了聊学术和人生之外,我还会和老师聊以前的历史以及如何看待历史。说来也凑巧,胡师原来是做历史的,后来转入哲学。而我的经历恰恰与他相反,我是哲学出身,没有想到后来不得不转入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这一度使我感到力不从心。我经常通过电话,向老师诉说我研究过程中遭遇的困惑与问题,他每次都耐心解答。我说做哲学,写哲学论文基本上有个不错的想法就可以一蹴而就。现在写历史类的文章,感觉特别琐碎,有挖掘不完的材料,而且杀青之后总会发现遗漏或者存在弄错一些细节的问题。胡师同意我的观点。他说,历史着力于还原事实,常常被时代的发展拖着走。而哲学、文学则不一样,往往能够超越现实,有着较强的时代引领性。改革开放之后,一些新思想出现在哲学、美学、文学领域,而历史学领域则明显反应较慢。
我非常服膺胡师的是在这样一个泥沙俱下的时代,依然能够那么“纯粹”!他真的是一位纯粹的知识分子,纯粹的书斋型知识分子。不仅如此,他心思单纯,与人为善,从他身上完全没有那种世俗的“油腻味”与“江湖气”。甚至,你会觉得他不谙世事,远离凡俗,完全沉浸在个人的内心世界。我问胡师:“您创作的高峰期在什么时候?”他说,四十来岁。想我已入不惑之年,倘使不抓紧大好时光,可能真的要落入孔夫子所说的:“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的境地。虽然相隔千里,对照吾师,吾深感惭愧。饕餮光阴不说,就集中思虑,一心向学这块,亦不知相差若何!
三
老师刚退休的时候,本来计划全家一起出去旅游。结果,体检发现师母患上了肺癌,而且保守估计,很难撑过三个月。当老师告知我这一消息,我连忙赶到北京,去医院探望。让我震惊万分的是,此时的老师虽然精神状态尚佳,但是已是满头白发,掩饰不住的憔悴。我读博那会,他近60岁,保养极好,至少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小许多。于是,我有了大胆地猜测:为了老师的学术,师母应该是包揽了全部的家务。以致于,当家庭变故出现的时候,老师显得力不从心,无所适从。后来,我斗胆向他说出了我的想法。他说我的判断是对的。我说:“老师,我们作为人都是有限存在者,某一方面有强项,可能另外的方面会出现弱项,毕竟我们的时间与精力是有限的。”做学问,有个贤内助太重要了!钱穆先生学术成就非凡,其实与他两位夫人的功劳有很大关系。在大陆的时候,钱先生与张一贯女士育有五个子女,全赖张夫人一手撑起家庭的重担。据说,钱先生做研究时,决不允许孩子在门外发出声响,以免分散他的注意力。离开大陆后,钱穆先生幸运地娶了胡美琦女士为妻。胡女士不仅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的生活,而且在他晚年失明的情况下,充当他的“眼睛”,陆续协助钱先生整理和出版了近百万字的学术成果。当然,遇到师母,胡师无疑也是幸运的!然而,师母的病情对于一贯在生活上“养尊处优”的他而言,确实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我倒是很佩服老师的研究劲儿,他说,为了照顾师母,他有意识地研究癌症,通过互联网的搜索引擎,他专门把医生开列的每一味药的药效与特性进行了详细地纪录。有一次,他带师母去化疗,医生开列的药物他觉得有问题,但还是不得不听从医生的意见。结果,师母身上确实出现了明显的不良反应。胡师向我讲述了癌症的一般机理。他说,癌细胞好比一支敌人的军队,化疗就是为了消灭这支军队。但是,你很难把这支军队全部消灭,只要有一个癌细胞漏网,它就会疯狂繁殖,故而,患者需要不断化疗。然而,化疗所起的作用仅仅是延续生命而已,病人却不得不不停地承受痛苦。师母的病情时好时坏,本来被宣布仅剩下三个月生命的师母,居然撑了三年九个月,不得不说是个生命的奇迹。在老师的精心照顾下,师母走得很安详!
师母去世后,老师的生活转入了常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构成了他生命的主旋律。在电话中,他向我提到他去了印度。他说,中国的建筑大多木制结构,农民起义或者造反运动出现通常会被付之一炬。印度建筑则多为石制结构,相对而言保存较好。越是历史悠久的建筑,越是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他还向我提及他去了南极,那种“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空旷感,让他不能自已,感慨宇宙造化的神奇。在他去世的那天夜里,他的同学提及他还去了新西兰,并在国外的大学图书馆久久不愿离去。在我校对的他生命中最后一篇文章中,他在批评康德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以美学的方式来寻找“安身立命”的“不朽”之道。显而易见,他不仅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
2023年3月5号晚上九点多的时候,我给胡老师打了个电话,询问他的近况。那时,他一直在通州的房子居住。之前,因为疫情,他一直很少出门,故而在2022年的12月份,并没有被感染。我询问他吃饭问题如何解决,他说简单做点面条,一顿管几顿。只是周末的时候,会到蓝旗营和儿子相聚。我说:“老师,您得照顾好自己,饮食方面一定要注意,尤其是要加强营养。”不料,8月27日晚上,我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大概十二点多的时候,他才给我回了信息。他告诉我一个震惊不已的消息。他说,最近去医院检查被诊断患上了左下颌腺癌。我上网查了一下,各种说法,乐观的悲观的皆有。但是,“癌”这个字眼本身就让人很是恐惧。老师虽然不是我的父亲,但是从精神意义上而言,他相当于我的父亲。我一直钦佩老师的为人,老师的纯粹,老师的简单,但是没有想到意外接二连三地出现。老师患的是口腔癌,我也不便打听到底到了什么阶段。他对我说,去北大肿瘤医院,排队排得苦不堪言。我说:“老师,您在北京就没有认识的人与这所医院有点关系的。”他说,他不太喜欢交际,故而基本上没有啥关系。哎,在中国这种人情社会,有关系,你可以绕开规则,走捷径;没有关系,规则成为不停折腾你的堂而皇之的理由。和老师打电话那会,小家伙说:“爸爸,你对你老师好尊敬啊!”我说:“是啊,爸爸一生非常幸运,遇到的老师都非常投缘。”可惜,我辜负了我的硕导,无法报答他的恩情。我的博导,他的学问我无法企及,但是,我对他的尊敬,那是由衷的尊敬!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关心他,协助他查找资料和校对文稿。因为,我知道:学术就是他的生命!
9月份的时候,我专程到北京去看望老师。他刚做了一个手术,大概是把腿部的骨头替换掉患癌部分的骨头,很是折磨!他身体很虚弱,正常的饮食无法进行,只能靠流食来维持。好在老师的妹妹赶来照顾他。他和我聊了两个多小时,他说学了哲学,毕竟对生死能够淡然处之,只是他担心自己手头的书稿能否顺利出版。他希望我能够帮他校阅书稿,我说:“老师,这对我也是一种学习,学生乐意为之。”大概到晚上五点多的时候,我与老师告别,便回到了宾馆。2024年的1月18日,突然接到师妹的讯息,说老师病危,住进了重症监护室,靠呼吸机维持。我一宿无眠,第二天一早,便乘车前往北京的医院。见到他的时候,已是下午一点多。我走近老师,握住他的手和他打招呼。他闭着眼睛,握住我的手,虽然显得无力,但是却有明显的颤动。到了晚上的时候,师兄和老师的家属都来齐了,便尊重老师的决定,回到蓝旗营的家中。老师在临终前,在纸上抖抖索索地写了几个字。一是“无悔”,算是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一是与亲人和我们这几个学生相约来生相见,“一言为定”。
2024年的1月20日1时40分,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老师,在学生的心目中,您是一盏“不灭的明灯”!您的思想,您的人格,您的精神,永远地激励着我们,照亮我们人生前行的道路!
(草成于2024年清明节前一日子夜,在这一个春雨凄迷的日子,谨以此文悼念恩师胡伟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