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邝启常(4)
回忆父亲邝启常 (4)
发布时间:2012-05-07 20:30
追求真理 矢志革命
—— 回忆父亲邝启常的点滴往事
(四)
延安,是当时无数怀揣抗日救国大志的青年向往的地方,也是中共中央培养和训练党的干部的中心。抗战时期在延安举办的中共中央组织部训练班,课堂坐落在延安城凤凰山麓,是一所培训党的工作干部的学校。中共中央组织部当时的任务是管理党政军民学各类干部的调动与配备,各地党委的组织工作,各地人员来往的输送,以及党员和干部的培训教育等。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亲自兼任组训班的主任,王德(后来,1939年,任中组部地方工作科科长,在全国胜利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任副主任。邝启常抵达延安,由组织上安排到组训班,和其他学员一同学习党的建设、党的基本政策、以及公开斗争、秘密斗争和时事等课程。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毛泽东也曾亲临组训班给学员们讲课,讲授著名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深受教员和学员们的崇敬和欢迎。邝启常在组训班的学习,不但加深了基本理论的认识,并且懂得了学习与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很快,邝启常又被调入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马列学院位于延安城北七、八里地的蓝家坪,学院校舍设在土石山上的窑洞里,与杨家岭隔延河相望。
马列学院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五日成立,张闻天任院长,早年留学日本的王学文任副院长,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创办的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为重点的干部学校。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经常为学院师生授课或作专题讲演、报告。马列学院的学员,一部分是参加革命战争多年,或在国民党统治区做过多年地下工作的老干部;另一部分则是知识青年党员,而这部分人在入学之前,绝大多数先经过抗大、陕北公学、中组部训练班以及中央党校的短期学习。
邝启常作为学员,在马列学院的“中国问题研究室”工作学习,并担任党支部书记和助教等职务。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杨松,和时任毛泽东学术秘书的陈伯达为研究室指导员,邓力群为研究室主任。学员们都住在同一个大窑洞里。同期的学员里,还有他的好友、曾东渡日本留学在中共东京支部领导下参加抗日救国活动的黄乃(在“哲学研究室”学习,之后同在敌工部工作)。邝启常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政策,他勤奋、好学,受到毛泽东的表扬。
通过在马列学院的学习和锻炼,让邝启常不但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还加强了党性锻炼和修养,这对他一生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起了决定作用。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一九三九年春季,为了克服经济困难,中央号召各机关学校实行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自救,就近开荒种粮。在主任邓力群带领下,邝启常和研究室的其他学员就近在校舍的窑洞旁边不远的山坡上开垦荒地。也是在这个时期,以及在后来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他学会了纺纱纺线、缝补衣裤等。让邝启常没有想到,这一延安时期学到的技能,三十余载之后,竟在“文革”时期孤独的“干校”生涯中让他“意外”受益。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同时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根据对日作战的新形势,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加大了敌军工作的力度。为加强对敌军工作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设立敌区工作委员会,总政治部设立敌工科(1940年扩大为敌工部),八路军各师、旅、团也相继成立敌军工作部门。总政治部提出了敌军工作的方针,要用各种方法削弱和降低日军的战斗力,促进日军的厌战和怠战情绪。出于抗日战争需要“知己知彼”,在战略和战术层面了解、研究敌人,敌工部还需要为中央的决策提供信息。
一九四一年,邝启常奉命调到总政治部敌工部。原任马列学院副院长的王学文这时任敌工部部长(1940年),早年留日归来的李初梨任副部长。邝启常任党支部书记,并在“日本问题研究会”担任研究员工作。
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有组织、正式的日本问题研究也就是从那时的敌工部开始的。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六日,具有共产国际领导人和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双重身份的野坂参三(冈野进,在延安时期化名:林哲)秘密来到延安开辟反战运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总政敌工部要调查、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实际情况;开展对前线日军士兵的宣传工作;做好日军俘虏的教育工作。继而,敌工部展开一系列有关工作:创办“日本工农学校”(1941年5月)、开设日语播报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广播(1941年12月3日)等。特别是,在兼任顾问的野坂参三指导下,组建了“日本问题研究会”,按照中央的指示,研究会做了大量对日调研等的重要工作,其中包括:编辑了介绍一般日本知识的《日本便览》(1941年5月15日),讲解日本的国体、天皇制、军部、军国主义、社会组织等情况; 创办了专刊《敌国汇报》(1941年4月),发表有关日本政局和军事方面动态的研究论文;“日本问题研究室”还专为给《解放日报》创办了半月刊《敌情》副刊(1941年9月27日),主要刊登日本动态、分析日本时事的评论和介绍日本知识的短文。时任野坂参三研究秘书兼研究室组长的黄乃,就是在《敌情》上发表著名的文章《南进还是北进》,准确地推断了侵华日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 这一分析推断,随着日本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得到验证之后,曾经轰动一时。《敌情》副刊也是毛泽东当时必读的重要刊物之一。
一九四一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邝启常先后在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任党支部书记、研究员。这几年里由于条件艰苦,他经常只能在延安窑洞里微弱的油灯下,阅读分析、翻译整理日文资料。他不懈地忘我工作,为中共中央抗日战争的决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使他本来已经深度近视的双眼越发严重,但是邝启常对此却从来无怨无悔。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延安,有一所由毛泽东倡导、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大学——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女大”)。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前建立的唯一一所女子高等学校(1939年7月成立,1941年9月与陕北公学一同并入延安大学)。“延安女大”一直受到延安党政军领导和干部高度关心与支持,两年间它培养出了上千名妇女干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出入同一窑洞的邝辉军(后来成为梁湘夫人)、叶群(后来成为林彪夫人)、薛明(后来成为贺龙夫人)等,都在这里学习和工作。就是在“延安女大”,邝启常遇到了一位影响了他的后半生的青年学员:文耘(李平祝)——我们的母亲。文耘十六岁那年,就已经在当地(广东鹤山)县立中学任教,从那时起她就开始阅读进步报刊,以及秘密发行的中共地下党的刊物,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她经常回家乡发动村里的青少年成立读书班、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和组织募捐支前工作。一九三八年五月,文耘年纪不满十八周岁就离开家乡,在胞兄李超(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时任“抗先”总队部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建国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人大”常委 等)的指引下,经广州八路军办事处云广英介绍,只身一人奔赴陕北。她一路躲过日军飞机的轰炸,沿途穿过国民党反动派暗地堵截进步青年奔赴延安的一道道封锁线,终于在七月三十一日抵达延安。后来,文耘在“延安女大”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青年时期的邝启常有着自己的浪漫情怀和个人魅力,同样更有救国报国的远大理想。邝启常早年在广州新闻学院组织 “时事问题研究会”活动期间,有一位勤奋好学、成绩优秀的知识女性张健平(曾与邝启常是知用中学的四年同窗、后在慕德师范学校任主任、教员),她既是邝启常每一场讲习的热心听众,又是他报刊文章的忠实读者。她为邝启常充满激情的远大志向和抱负所吸引,相同的爱国情怀也使两人平添了许多共同语言,在广州的那些年里,邝启常与她维持了一段亦师亦友的纯真感情。作为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新青年,邝启常对婚姻有他自己的追求。在给胞兄邝杞文的家书中,他曾写道:“关于婚姻一事,仍然在考虑中,还不敢轻易决定。因为我所理想中的侣伴,不但是要对我诚实,同时还要在学问上、思想上、行动上,与我相同。……我希望家里不要为我的婚姻问题担心,我自己总有把握。婚姻是大事,要三百思而后可行。” 邝启常为了理想和抱负,北上北平、东渡日本、又奔赴延安,他把个人的理想、前途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走上了一条革命者的道路。在陕北延安宝塔山下,邝启常遇上了自己人生道路上志同道合、心心相映的伴侣 文耘。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事业,让邝启常和文耘最终走到了一起,他们在延安期间结成了夫妻。在当时炮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以及后来硝烟弥漫的解放战争时期,他们一直不准备生育子女,而共同誓言为了党和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他们一直都坚信并憧憬着未来,期待着让自己的子女生长在属于人民的和平年代。历史最终证明了他们的远见。直至建国后的一九五二年,他们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女儿。
一九四四年,由于苏联红军的全面反攻,美英军队开辟第二战场,世界反法西斯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逐渐失利并开始由攻转守,为了解决日益匮乏的军队补给,其在中国大陆的军队开始作垂死挣扎,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在迎战日军的过程中先后丢掉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片国土和一百多座城市。为迎接抗日战争的大反攻,党中央决定在巩固华北、华中的同时,派多支作战部队和干部工作队,开赴华中,挺进华南,建立湘鄂赣边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提出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三月下旬,王震、王首道率先领导三五九旅“南下第一支队”进入湖南;五月十八日,中央又决定抽调延安部分两广和湖南的干部,与延安警备一旅一部共同组建“南下支队第二梯队”(文年生为司令,张启龙为政委,陶铸为副政委)。旗下的南征干部大队(即“东干队”——广东干部大队,武晋南任队长)组织了200余名干部队员,邝启常被选入担任干部大队的组长,与梁湘(后在改革开放初期任深圳特区党委书记、市长)编在同一个干部队。六月,“南下支队第二梯队”的“南下第二、三支队”先后从延安出发,挥师南下。十二日,延安各界在飞机场举行了盛大的“南下支队”欢送仪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陈毅、聂荣臻等亲临检阅部队,贺龙发表讲话。随后部队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穿越同蒲(【注五】),经太岳山(【注六】)革命根据地后南下。
出发当天,部队就行走了八十里路。邝启常在延安工作的这些年里,“眼睛已经深度近视,在行军途中,梁湘处处关照着他。有一晚,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队伍从一路变成八路纵队迅速行进,邝启常突然走得磨磨蹭蹭,口里嘀嘀咕咕,梁湘一边紧紧拉着他走,一边问他:‘你嚷什么,还不快走?’他懊丧地答道:‘我的眼镜掉了!’近视眼失去眼镜,眼前矇矇眬眬,举步维艰,无怪乎他叫苦不叠。后来经过多少艰辛,队伍穿过一个小镇时,给邝启常买到一副镜片中有密密圈子的眼镜,他才轻松了许多。”(【注七】)
七月底,美、英、苏在苏联的海滨城市雅尔塔召开会议,苏联以得到蒙古、千岛群岛和中国东北部分铁路的管辖为条件,决定近日出兵中国东北。蒋介石为了达到盟军不得将占领防地交与八路军、新四军为目的,派代表同苏联政府签定了协议,得到了苏联的许诺。八月八日夜,苏联对日宣战,一夜之间苏联红军一百五十万人,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向侵占中国的日军发起了全面进攻,素称精锐的日本关东军连遭失败。八月六日、九日,美国分别向日本广岛、长崎各投下了一枚原子弹。十日,日本投降。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邝启常跟随大部队走到陇海铁路旁边的河南新乡,准备二渡黄河,这时传来消息,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了。整个队伍沸腾起来,大家奔走相告,邝启常和所有干部战士一样分享着抗战胜利的喜悦:八年浴血抗战,终于迎来中国的最后胜利。
八路军迅速挺进华南,早被国民党视为心腹之患。日军投降,国民党却集中优势兵力对“南下支队”前堵后追,使部队面临极大的困难。时局发生巨变,中央审时度势,调整了工作方针,实行收缩南方、发展北方的战略。八路军“南下支队”奉命挥师北上,要精减行李,徒手行军,昼夜兼程,转向东北三省,接收原被日本鬼子侵占的地方。“南下支队第二梯队”的先遣战斗部队,由张启龙带队骑马先行。邝启常所在的干部大队在武晋南带领下随即徒步紧跟。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行军,转战来到东北向陈云领导的东北局报到。之后,邝启常被分到吉林省工委,书记是张启龙,武晋南为副书记。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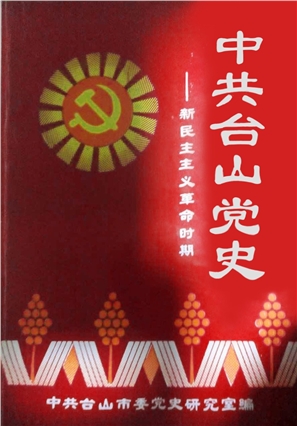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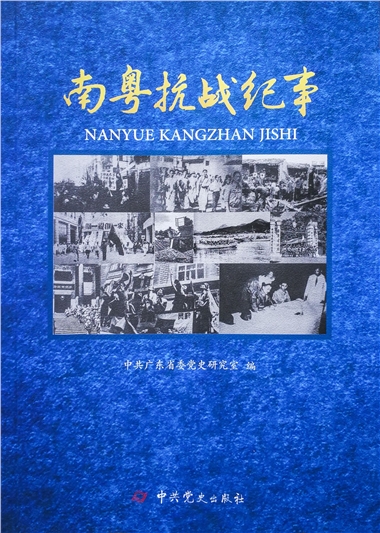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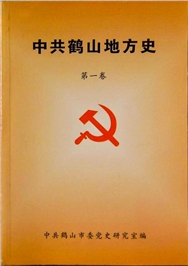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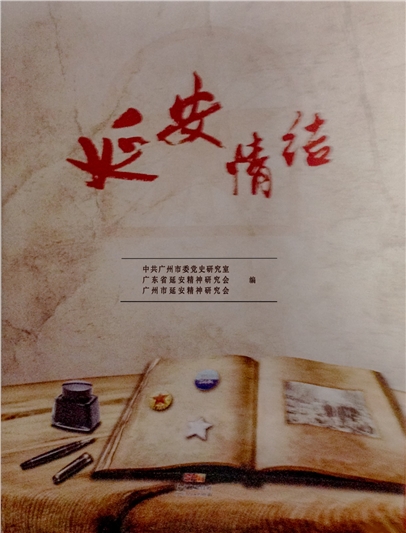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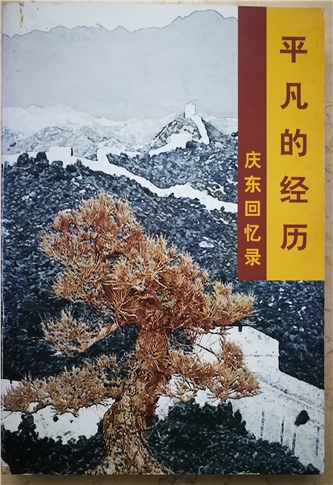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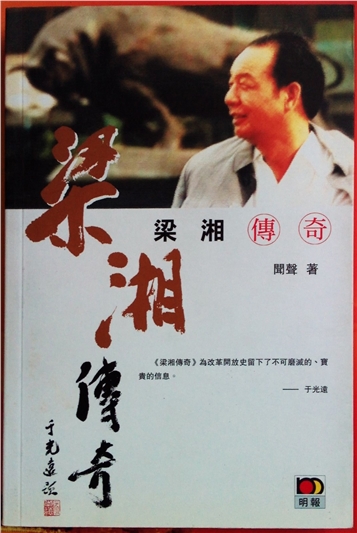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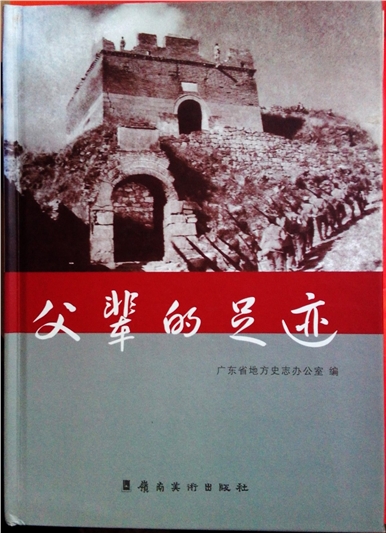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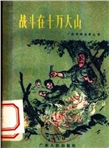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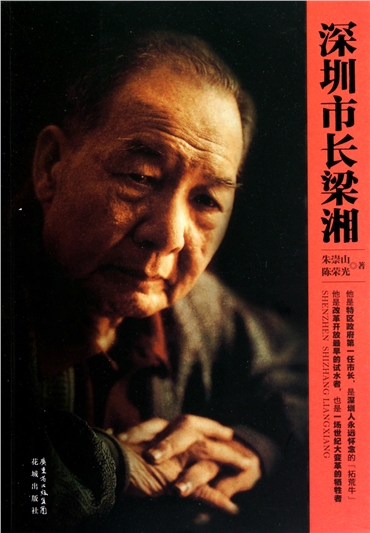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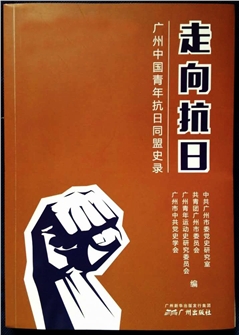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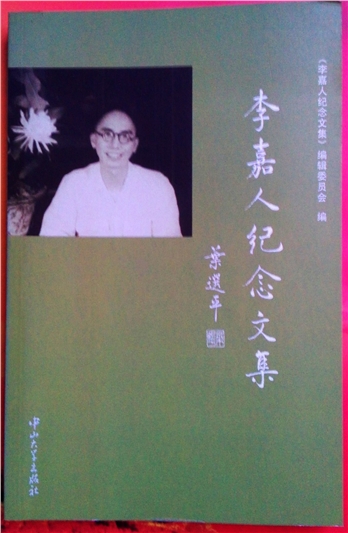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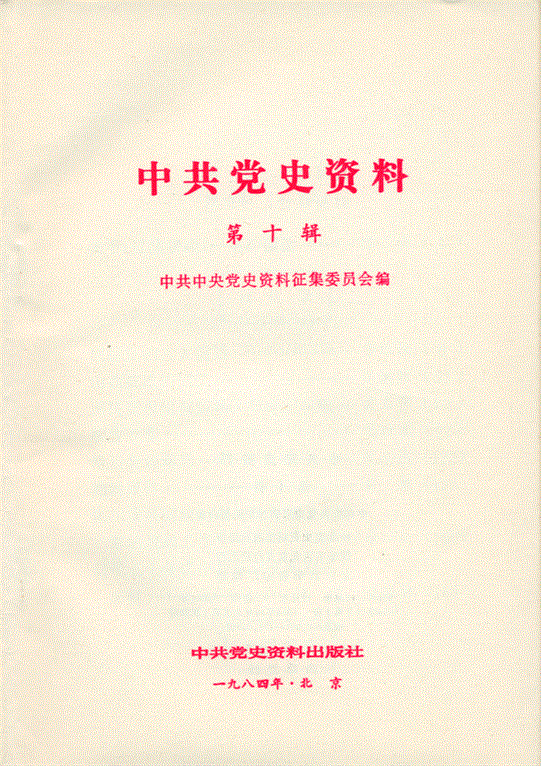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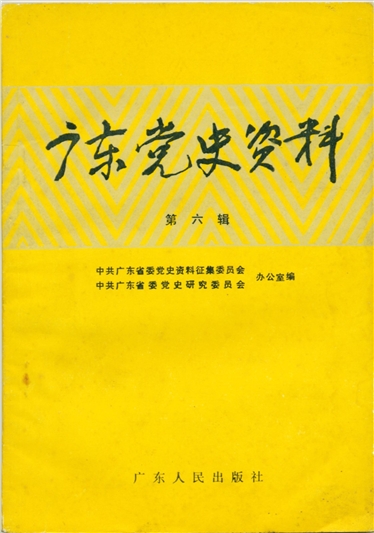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