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5-08-19 21:45:33
发布人:
天府霞影
风云日月八千里(3)
十三,与车耀先的交往
到成都后,于浣非为了继续从事唤起民众的抗日宣传工作,需要有一间安静的写作室。家里太吵,不能写作,他在外租了一间屋子搞创作。后来他的四妹妹来到成都,在祠堂街租下铺面,开了一家书店,楼上就成了于浣非的写作室。
他在成都又创作了一个展现沦陷区女性抗日杀敌爱国事迹的剧本<大红鞋>,(该剧本语言朴实,一些习惯语气的风格,与他过去写的<鞭子>的风格酷似)以及许多文稿、演讲稿。(这些剧本、文稿,是小儿子在上世纪50年代从李相云家中的积满尘土的大柳条包里发现的)。
这间书店,吸引了众多东北流亡人士和青年学生。他们忧国爱国,常来看书购书,交流信息。书店的兴旺,引起了街对门一家餐馆老板的注意。他常过书店来与这些东北人士交谈,很快与于浣非成了朋友。他就是时任中共地下党四川军委书记,“努力餐”餐厅的老板车耀先。
车耀先多次来家约于浣非外出办事,李相云说他像一个小老头。他热心介绍于浣非的大儿子二儿子参加他领导的群众组织<大声社>的活动。又与于浣非李相云商议,把他们的二儿子送去延安。(最终因车耀先被捕而未成行)。车耀先还介绍于浣非大妹妹的独生子去一所本地有名气的中学就读(后来他成为北京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知名教授)。
十四,不畏惧白色恐怖,以公司名义担保,从监狱救出中共女党员
抗战期间,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进成都市宁夏街监狱。当时车耀先已被捕,成都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于浣非受邀去重庆见了周恩来。那时李相云经营的太白牙粉公司,在成都西门一带有些名气。于浣非回成都后,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和家人的风险,李相云以太白牙粉公司的名义作为担保,将这位女共产党员袁志杰(音)营救出狱,接到家中调养休息,住有月余。她后被安排去了延安。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审干之时,从北京来的外调人员找到李相云查证此事,方得知袁某己是北京市级一个部门的领导。李相云为她说清楚了这段历史。袁某从此渺无音讯。
十五,抗战胜利,于浣非遗妻弃子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于浣非与几位妹妹及妹夫聚集在成都金牛坝大妹妹(于汝洲)家中,对当时的时局有过一番评议。他们曾经追随孙中山的理想,抗战中从事爱国抗日活动,又在国民政府的机构中供职,现在抗战即将胜利,对未来应作一个展望,并作抉择。李相云静静地在一旁关注着他们议论。
在对国、共两党对比以后,于浣非清醒地断言:国民党政府太腐败,不得民心,未来的天下一定是共产党的。其实,这也是在场的所有人的共识。但随后的行动,他们并没有选择新的道路,而继续在腐败的国民政府中谋职,参与对敌占区的接收工作。
抗日胜利后,于浣非去重庆,从国民党政府谋取到东北救急总署下一副署长之职,就离开他的家人去了东北。离家前夜,为了旅途的安全,在昏暗灯光下,李相云一针一线地为丈夫的内衣内裤缝上两个布包,用以隐藏钱币和重要的物件。于浣非许诺回到东北安排好后,就接她们母子回东北。第二天,就离家而去。
不久后,于浣非的大妹一家人和于浣非的母亲一行,分乘几辆人力车也离家而去,此一去也成为永别。
几十年后,九十高龄的于汝洲,从台湾托她在清华大学的独生子转给于浣非子女一封信,她信中谈了她永远无法忘怀的一幕。在一九四五年她们离开成都的那一天,于浣非只有四岁的小儿子紧紧地抱着她的腿,哭叫着不让她走,当黄包车移动后,听到从背后传出哭叫声:我要去找爸爸,我要去找爸爸……她回过头来,见到小小的孩子大声地哭喊着,拼命地追赶着那几辆载着她们一行人的渐渐远去的人力车。
被遗弃的子女们早已没有记忆,而追随国民党去了台湾的于浣非的大妹妹,几十年间,却把这悲惨凄楚的一幕,清晰地深深的刻在了她的心中。
十六、国破家散,夫离子亡,李相云连遭沉重打击
于浣非离去,李相云成了这五兄妹的唯一依靠。更加艰难的岁月开始了。打击和灾难接二连三地降临,李相云以博大的母爱和坚强的意志,与恶劣的社会环境抗争,用她那矮小的身躯和柔弱的肩膀,奋力撑起这个六口之家。
过去李相云主内,丈夫主外,于浣非虽然常年不在家,但涉外之事仍得他斡旋。于浣非的正直、才气、干练,李相云的仁慈、宽厚、简朴,深得友人和邻里的赞许、敬佩。过去家里有一位父亲和丈夫,孩子和妻子会自信许多,轻松许多。
现在商店的生产和经营就靠李相云一人里外维持照应。四个大孩子,正分别就读高中、初中、小学,只有最小的儿子还没有上学。学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还有六张嘴要吃要喝,还要付房租。在旧社会,一个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女人,要有怎样的能耐,怎样的坚毅,怎样的精神才能挺得下去。
那时号称的公司,其实就是一间铺面的商店,楼上卧室的半间和后面院子一间十来个平方米的屋子当作坊。早前几年,请了两位管供销的先生,还有一个打杂的学徒,丈夫走后,他们都留下来帮助李相云,李相云待他们也如同自己的儿子。产品的生产仍然是她自己操持,配料、过筛、合成都是她自己劳作,早晨天不见亮就起床,晚上十一、二点钟还不能就寝。
抗战胜利后,外国洋货和上海货、广州货大量涌入内地,生意日趋衰落,逐渐入不敷出,只好辞退两位员工,只留下一位先生帮助经营。这位先生是川北阆中人,父母早亡,除有一位表兄外,别无亲人。他仅比李相云的长子年长几岁,初中文化,好学又能吃苦,正直本份,作风正派,李相云将技术传授给他。他敬重她的人品,主动要求认她为干妈,成了这个家庭的正式一员,对李相云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成都解放后,他报名参加土改工作队,回来后被选为街道居委会主任,热心公益事业,但仍然在李相云家居住,协助生产经营。
直到一九五六年合作化运动,李相云和他都全心身地参加了化工手工业合作社,把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入了社。她每天步行几十分钟去城外的合作社上班,早出晚归。这位先生被选入合作社的领导班子,他结婚后有了自己的家,这才离开了干妈的家。几十年,她们一直保存着亲情和友情。
于浣非走后就渺无音讯,他没有兑现行前对妻子儿女许下的安顿好后把全家接去的承诺。不过当时国家前途渺茫,内战一触即发,也使他无法实现他的承诺。
李相云坚强地一人独挑家庭重担,起早贪黑,如牛负重。日积月累,她双手的皮肤被化学药品灼烧得布满粗糙干硬的裂纹,每天涂抹许多凡士林,皮肤也不能滋润。她晚上在床上抚摸小儿子时,儿子对母亲说:“妈妈把我摸得好疼”。
从这段时期开始,晚上不能入睡时,李相云常常给小儿子讲述她的人生的痛苦和艰辛。她讲得最多的就是,由于没有文化,在社会上,在亲戚中,感觉到被人瞧不起。再怎么受苦受累,也难以得到他人承认。在外办事很艰难,吃亏上当,有理也说不清楚。所以她下定决心,自己再苦再累,也一定要让几个孩子把书读出来,今后才能在社会上立得住,站得稳。
大儿子、三儿子及女儿学习都很努力,在各自的学校表现很优秀,成绩名列前茅,也是学生组织的活跃分子,令李相云很欣慰。唯有二儿子不肯用功学习,常常和几个纨绔子弟逃学,甚至考试也不去,让李相云很伤心。给他换了几所学校,仍然顽性不改。最后只有停学,让他在家帮助经营生意,但这也收不下他的心。这时,国民党反动派要打内战,欺骗宣传,说是青年学生受一年军训回来可以保送读书或安排工作。他们几个逃学的同学以为这是捷径,相约去受训当兵。当兵也吃不下苦,又逃跑回家,军官追到家里抓人,没处躲藏,被迫又去当兵。后来国民党反动派把他们送去当炮灰,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在祖国的西北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革命军人,二儿子终于走上了正路。现在老了,享受着离休干部的待遇。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大儿子以优异成绩从华西协和高中毕业。他中学时就喜爱写作,英文也好,常常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翻译作品,还尝试电影剧本创作。他的志向是成为一个电影人,去长春电影厂工作。因生病失去上大学的机会,他日夜等待父亲给他寄路费,以便回东北实现自己的梦想。可许多天过去,毫无音讯,他失望了,连续多天出外找工作未果。
由于大儿子的早熟、聪明、优秀,父亲的绝情,以及内战的现实,让他对家庭和国家都绝望了,于是选择了死亡作为抗议和解脱。一天,在外面寻求出路,跑了一整天的他很晚回到家,什么也没说就倒在床上睡去,李相云以为他太疲倦了,没去惊动他。第二天早上叫他起床吃早饭,发现他已不省人事,床头有一个装过安眠药的空药瓶。赶紧把大儿子送去医院抢救,在医院昏迷两天后去世,年仅二十岁。
这对李相云的打击太大了,伤心了许多天也不能恢复。当年成都的新闻媒体,对于浣非的大儿子之死,作了醒目报导,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同情。
李相云一下就苍老了许多。其实,她在几个月之前,就得到大妹妹寄来的信,告知于浣非己另有女人的消息。于汝洲在信上写道:“嫂子,你快来北平,大哥己经有了另外的女人,他借口说是为了照料母亲,嫂子你快来吧!”
为了身边几个子女,李相云默默地吞下泪水,更把全部心血消耗在子女身上。她坚强地挺着,更加奋力劳作,起五更睡半夜,希望把生意做上去,好养活子女,供他们读书。她生存的唯一目标,就是把孩子们培养成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
这年,最小的儿子己经上初小了,也懂些事了。小儿子一直是和母同一张床睡觉。不管多晚,李相云在睡前,都要跪在受难的耶酥圣像前作祷告,向耶酥诉说心中的苦痛,以求得到神的帮助。有时候,会用她那凄楚的带些颤抖的低音,轻声哼起<苏武牧羊>和<松花江上>这两首悲壮哀婉的歌。她用这两首歌抒发内心的痛苦,也用这两首歌激励自己的斗志。这是儿子长大之后才明白的母亲的情怀。
李相云抑压住内心极大的伤痛,用她那粗糙的手,轻轻拍打着小儿子娇小的肉体,把他带进梦乡。她欣赏着睡梦中儿子平静的小脸时,母亲的心向上慢慢地升腾,直到和圣母的心融为一体。一个家庭可以没有父亲,但绝不能失去母亲,母亲就是孩子们的圣母。
十七,社会同情弱者,上帝之手帮助她
大儿子的死被报纸报导后,李相云一家受到好心人的关注。小儿子就读的树德小学的王校长,是同一条街的邻居,也是这条街的保长,他来到李相云家,深表同情,他希望孩子不要辍学,可免除学费,希望能继续在他的学校读书;广益小学是教会学校,吴校长是位基督徒,他也来到李相云家,让小儿子到他的学校读书,也免除学费。对两位老校长的盛情,让困苦无助的李相云感动万分,难以取舍。因为是教友,小儿子又是在那里出生的,所以,最终选择了广益小学。
后来,星期天,李相云常常带小儿子到礼拜堂做礼拜。礼拜堂就在广益小学校的门口傍。每次参加礼拜的人有四、五十人,六、七十人不等,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穷人富人都有,他们亲密无间坐在长长的椅子上。传教的牧师和蔼可亲地讲述圣经上的故事,传播着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关爱,要帮助穷人和有困难的人。讲完故事就开始唱歌,集体唱赞美诗,接下来就是表演节目。
一个瞎子在信奉上帝以后,眼睛睁开了,见到了光明;一个满脸麻子的有钱女人,在神的指引下,她做了帮助穷人的好事,最后脸上的麻子没有了,变成了漂亮的太太。 孩子天真无邪地问母親:我看见她脸上的麻子是用墨水画的,用水洗了就漂亮了嘛,为什么会是帮助了穷人就变漂亮了呢?母亲赶紧用手捂住小儿子的嘴:不许乱说。
做礼拜的会上,也有人提议欢迎某先生唱歌、某太太唱戏助兴的,也做类似击鼓传花的游戏,有时也搞慈善募捐活动,穷人富人各尽所能,慷慨解囊,有时还放无声电影。
小儿子此生第一次看电影就是在这间礼拜堂。白墙当幕布,只见房子从小变大,人在街道上走路像是在跳,又像在跑,车像在河里的船,街边的房子迎面飞来,又向两边倒下去……看得人有些头晕目眩。虽然觉得很新奇,但感觉电影既不好看,更让人不好受。等孩子读中学后才知道,那是当年看电影离银幕太近的缘故,房子也没有飞,也没倒,是镜头移动的效果。
李相云在失去丈夫和大儿子后,在基督精神的感召下,更忘我劳作,用瘦弱疲惫的身躯,艰辛地支撑着家这片天空,想方设法让剩下的三只小鸟,羽翼逐渐丰满。
三儿子在省艺专学画,女儿在华美女中初中读书,为了让他们专心学业,李相云让他们住校,每礼拜天回家一次。这天家里会做有肉的菜,全家人打个牙祭。如果没有吃完,有剩下的肉菜,那就成了小儿子的特权。有时候另外炒点咸菜,装个小瓶子,让女儿带到学校去下饭。母亲成天劳累,有点好吃的她总让她的子女们多吃,她自己只尝尝。
李相云一生克勤克俭克己,从不浪费剩菜剩饭,就是有馊味了也舍不得倒掉,重新热热吃下去,还说 :“拉拉肚子也好,治便秘”。直到她晚年衰老去世,都是如此。李相云的这一传统被她的小儿子继承下来,现在他成了他家里的泔水缸,无论是饭菜变味或是牛奶发酸,都经处理后由他独享,妻子儿子们是不会分享的。
- 上一篇:风云日月八千里(2)
- 下一篇:风云日月八千里(4)
到过这里的访客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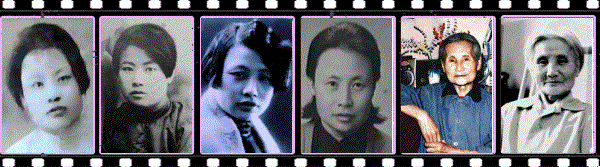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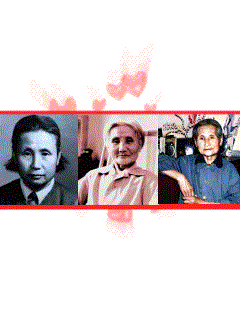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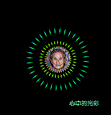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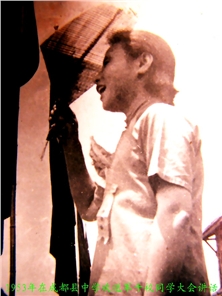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