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5-08-17 22:02:34
发布人:
天府霞影
风云日月八千里(2)
六、不畏艰险不辞辛劳救助难童。
救助和疏散沦陷区难童的工作十分重要。当时这项工作是国共两党共同关注的,宋美龄、李德全、邓颖超是这项工作的主要组织者。于浣非的大妹于汝洲,从开始就参与了这项艰巨而崇高的工作,并成为重要骨干。她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发起人之一、筹委会成员、理事会理事、宜昌战时接运站接战主任。
二妹(于淖汶)也是医生,也参加了救助疏散难童的工作。她们到战区去救助难童并护送到武汉。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前,大批难童急需往大后方撤退。由于日寇逼近,武汉大撤退迫在眼前,水路陆路运力严重不足,交通运输拥挤不堪,数千难童,需要分散成多批护送。每批几十人不等,配有带队的教员和医生,以便照料这些可爱又可怜的孩子们。
于浣非担当了第十三批难童的医生兼教员,(另外还有两位女教员)组织率领四、五十名年龄从五岁到十五岁不等的男女孩子,登上撤退工厂设备的轮船。于浣非的家人也成为工作人员随队而行,李相云把自己的孩子和难童们聚在一起同等对待。孩子们的衣食住行、饥饱冷暖、拉屎拉尿都得管到。从汉口逆水航行五天才到达宜昌,在宜昌换小船才能继续西行。到达宜昌后,另两女教师因怀孕数月,工作已难胜任。候船期间,于浣非将几个儿子和难童组成歌咏队,上街演出并到医院慰问受伤抗日将士。他二妹率领的另一批难童也到达宜昌。在宜昌侯船两个多月,直到一九三八年九月才抵达四川重庆。
几年来一直和于浣非一家相邻而居的好朋友赵惜梦一家人告别去了昆明。临产的那两位女教员也辞职而去。
于浣非一行又换乘两辆军用卡车,饱受颠簸呕吐之苦后,到达四川省会成都,把这些儿童移交给设在成都皇城内的保育院。
几年后,读中学的于浣非的二儿子,在学校与几位己是中学生的难童不期而遇,惊喜不已。
成都最终成为于浣非一家五年多流亡生涯的终点站。
在祖国的大后方,有了一个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相对安定的栖身之地。但是,国难不了,家难怎消?此后许多年,新的一轮又一轮的打击和磨难接踵而至。
国难造就了中华民族又一位崇高女性;家难锤炼出人世间再一位伟大母亲。
七,定居成都,为活下去重新创业。
到成都后只能暂栖旅店安身。在武汉出生的老五,由于流亡途中李相云的劳累和缺乏营养,儿子先天发育不良,一直生病,得不到有效治疗和营养补充,再加上流亡途中的颠沛折磨,到成都后不久,就在祠堂街的旅馆里夭折了。
但这并不影响于浣非的爱国热情,一九三九年,他联络在成都的东北藉的文化艺术界的同仁们,在祠堂街的新又新电影院,举办了纪念著名苏俄作家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的活动。以示对红色苏联的敬意,和对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拥护。这也是孙中山先生去世时,他誓言要继承孙中山先生意志的的又一体现。会场中悬挂的高尔基像,就出自于浣非的手笔。他的大儿子是参加纪念活动人中唯一未成年人。
经过几次变换暂住地,终于在市内青龙街口的广益小学空置的校舍内安居下来。这是因为躲避日寇飞机的轰炸,小学疏散到西城外去了。于浣非的家就在小学内最后面靠左角的一间教室。安顿下来以后,性刚嫉俗的他,整日在外忙他的救亡事业,一心为国事奔波,却不知生财养家。
为了养家糊口,李相云决定重操旧业,租了一间店铺舖,自产自销化妆品和卫生用品,担负起理家创业,哺儿育女的重任,日子过得颇为劳累而拮据。
八,家庭会议,决定即将出世的孩子的命运。
到成都安定下来之后,李相云又怀上了第六个孩子。这第六个孩子的降生,却成了一家人面临的大问题。为此一家人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议题是:一、是否要这个孩子;二、给这个孩子安排出路。决议是:生下来,送人。
于是通过基督教会,(于浣非夫妇早在哈尔滨时,就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找到一户有文化教养的人家,先生当时在成都的一所著名大学任校长,夫妇婚后多年没有生育。他们互相了解后,彼此景仰,成为了朋友。
在成都几经日本飞机的狂轰乱炸之后的某一天上午,一个男孩从母亲的腹中,挣扎着来到这充满战火硝烟、罪恶累累的人世间。就在他对这陌生世界充满惊恐,发出愤怒哭喊的一瞬间,作为母亲的李相云就再也舍不得将孩子送给别人。
从此,这孩子成了这位母亲的最爱,成了她一生最重的负荷,成了她甘愿受尽人间苦难的原动力,成了她期盼美好未来的寄托,成了她在黑夜中倾诉悲痛的最佳对象,成了她在绝望时,能够刚强活下来的重要理由。
二十几年以后,这孩子己长大成人,参加了工作,从外地回成都探望母亲。他随同母亲走在街头,迎面过来一对老夫妇,他们热情地和李相云打招呼,并在街边交谈起来。这孩子主动离开远一些,以免影响他们谈话。李相云与二位老夫妇告别后,她告诉小儿子:他们就是当年准备抱养你的校长夫妇,他们刚才还向我询问你的情况。多么可亲可敬的老人呵。要是二十二年前这孩子成为他们的养子,那么这孩子今生将又会是另一番情景了。
九,更新名字,义重于天 。
为人平易慈祥的李相云,文化程度不高却深明大义, 在第六个孩子出生之后,她为自己的五个子女重新起了名字。过去他们叫大明、明明、世明、元龄,是做母亲盼望人世间的光明,国家的清明,而取明字为名。
在经历九一八事变,五年多背井离乡的流亡生涯,目睹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给东北同胞和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灾难的现状,李相云希望把这极不正常的世道纠正过来,她把振兴中华的希望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所以为自己的孩子重新更名为:正中、正华、正民、正之、正国。联起来就是正中华民之国。之前加个正字,其含意就是,把腐败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名不符实中华民国,纠正为名符其实的、真正的中华人民当家作主之国家。
李相云为五个子女取名的爱国之心,义重冲霄,天地可鉴。表现了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和胆识,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其伟大感人之处,堪比岳母刺字。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统治中国的国民政府的鹰犬嗅觉不灵,户口制度也不严密,否则一旦被追究,灭门之灾难免。
几十年来,李相云在遭受苦难,感到压抑悲愤时,就哼唱<松花江上>和<苏武牧羊>这两首悲壮的歌曲,以激励自己,获取生活的力量。
十,抗日救国,再担重任。
于浣非与在成都的东北藉爱国人士,发起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总部设在当时的抗战陪都重庆)。于浣非担任东总成都分会的宣传部主任,他还专为东总成都分会设计了一枚会徽。
东总成都分会从成立之日就设在于浣非的家中(青龙街119号)。许多爱国抗日人士常在于家进出,偶尔在于家短住几日的也有。李相云在生产经营店铺,挣钱养育五个子女的同时,还常要热情地接待这些来往的客人。他们多为爱国热血青年和中年人,比于浣非夫妇年龄小,所以,来客均尊称于浣非为大哥,尊称李相云为大嫂。他们中有作家、诗人、画家、演员、职员、医生、流亡学生、国民党军人和政府公务员。有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党地下党员。
多年来在李相云家的相册中,一直珍藏着他(她)们中一些人的相片,以及一些重大活动的纪念合影照。李相云常常翻开相册对他的老儿子讲述这些人的情况,一一道出他(她)们的姓名,回忆与他们相处的轶闻趣事。这也是她在困苦寂寞之时,与小儿子寻求慰籍的习惯。
可惜的是,这许多在白色恐怖中,都敢于保存下来的珍贵历史老照片,却在文化大革命的赤色恐怖中,被付之一炬了。最终只有: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六月,由新华日报馆印行的、封面有毛泽东头像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及中苏文化杂诗社出版的<苏联革命时代的游击战>丛书、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的<日寇暴行实録>等,被珍藏下来。
最初,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的会议和联络地点,设在成都东胜街的沙丽文舞厅,舞厅出入的人多,社会各界的人都有,对抗日组织活动有很好的掩护作用。因而一段时间并未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几个月后,发觉有陌生人盯梢,疑是特务,为安全起见,迅速将联络站也转移到于浣非的家中。于家就成了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的一个秘密联络地点。当时东北救亡总会总部的于炳然从重庆来成都指导工作,也在于浣非的家中住过几日。
日寇飞机轰炸成都后,于浣非参与四川成都的文化艺术界爱国人士,发起在少城公园举办了一次揭露日寇暴行,唤起民众的大型画展。就连当时只有十岁的三儿子,也到被轰炸现场,用画笔记录下日寇的无耻暴行。于浣非将幼子的作品送去参展,反响很好。
在汉口与于浣非家同住在一幢楼的赵惜梦的一家人,一九三八年八月从宜昌同船到重庆后,与于浣非家道别去了昆明,以后又去兰州。赵惜梦先后在两地创办报刊,并邀请于浣非作为报刊在四川的特派记者。于浣非不仅为他撰稿,还到兰州与赵惜梦共谋策划宣传救亡抗日之事。
十一,对肖军的特殊情结
肖军到成都后,将鲁迅先生亲笔为他题写的: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条幅赠予于浣非家。肖军在成都期间,与于家交往频繁,他还常和他的新婚妻子王德芬女士来到于家。他尊称于浣非为大哥,李相云为大嫂。因为肖军皮肤较黑,李相云则昵称他为 “黑小伙”。王德芬女士年轻漂亮,李相云曾误以为她是四川大学的女学生。一九四零年,在肖军夫妇决定去延安前,将他们无法携带的物品,一张方桌(桌子底面有墨笔写的肖、王二字),还有一本肖红的日记及杂物等,用木箱和大网篮装着,送到于浣非家存放。
原以为肖军夫妇去延安后,会回来取这些东西的,未曾料到,此去竟是他们一生的永别。
在抗战胜利于浣非抛妻弃子走了以后的岁月里,李相云的家搬迁了几次,宁可丢掉自家的东西,也要将肖军的东西一件不少地带走。新中国成立后,她一直等待他们的消息。当从报刊得知肖军和几位熟人受批判,她对肖军等人的命运感到担心。但不管怎样,总算又知道了肖军的消息。
李相云带着她的老儿子又一次清理了肖军夫妇存放的物品,将因屋子漏雨浸湿而发霉的印刷纸版,搬到院子里曝晒,然后再装入网篮,仍然妥为保存。极希望有一天肖军夫妇能来取走他们的物品。
直到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搬离原来较宽的住所,迁往只有一间屋子的住所,窄小的居所己无法存放这些东西,迫不得已,才将已经发霉的纸版,在炉灶中烧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旧家具都淘汰了,唯独将这张底面写有肖王二字的破损的桌子保留下来。
一九八零年,报纸上登出一篇写抗日时期肖军在成都的文章,李相云读报后,将肖军在成都时期的一些情况告诉她身边的老儿子,要他写一份补充寄去报社,该报转而将它交给了写那篇文章的作者---车辐。车辐曾热情去信邀约李相云的小儿子一见,因为其它原故,他没能前往见面,从而失去了与肖军取得联系的机会。
一九八八年,成都一家报纸上又登了一则消息,八十岁的肖军来成都,与老朋友作家车辐会面后,己经离去的消息。时年已是八十七岁的李相云得知此消息后,微微地笑了一下,她感慨地说:肖军也许以为我们不在成都了。次年李相云就去世了。
其实,肖军复出后,曾去过乌鲁木齐,见到于浣非的三儿子(从小就显露美术才华的他,己是新疆师大的美术系教授),并对他说:已搜集整理了抗日战争时期东北作家的资料,准备出一本有关的书,就缺你父亲的资料了。近二十年又过去了,肖军已去世十几年,不知他的遗作是否出版?
肖军留下的那张方桌仍被保留下来,虽然它已破烂散架,有些影响观瞻,但见此物,能让人想起父母那段流亡动荡、艰辛苦难又令人荡气回肠,终生难忘的历史。(2011年才将破损不堪的方桌丢弃)
肖军此生,常被置于人生长河的波峪浪尖,堪坷一世,褒贬不一。了解历史的人民自有公论。肖军是鲁迅先生的好学生。尽管他也难免有一些人性的弱点,但是,他与鲁迅一样,是中国人之中的硬骨头,不屈从权势,不奴颜媚骨,是具有中华民族最可贵品格的人。
十二,深入民间,救死扶伤
抗日战争胜利前的那几年,于浣非在四川省教育厅找了一份差事,名曰:“卫生视察员”,常常到四川各地州县的学校巡视,为学生体检,掌握学生的健康状况,为学生治病也为当地的穷苦百姓看病。他也去藏族、彝族地区为少数民族人民治病,不嫌脏,不怕累,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还随马帮一道徒步翻越鹧鸪山(夹金山)。他那些在艰苦岁月里,为彝、藏百姓治病,与穷苦老百姓打成一片的照片,头扎布巾,脚捆绑带,在野地大口进餐的镜头,就是真实历史的见证。
到过这里的访客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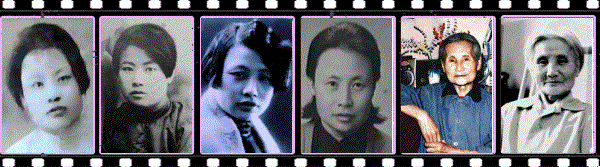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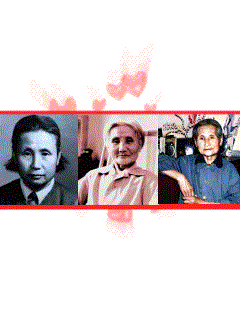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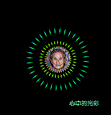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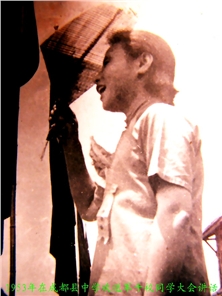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