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
2021年12月12日,夜里8点30分,武汉光谷高新园区,高新二路与郎日街的交叉口。
还是这样一个地点,还是这样一个周遭的环境,我再一次来到这里,来到这里去给母亲过这个七七日。
依然是那样的珠串一样的暗黄的灯光,依然是微风不起的天气,依然是暖暖的空间,四处没有人,偶尔有车辆经过也是一闪而过,丝毫不影响纸钱金锞子的摆放与燃烧。
在这片安静的黄韵的氛围里,我小心地点燃了纸钱和金锞子,看着那跳动的火苗,以及火苗中慢慢窜动的灰烬与火焰的连线,看着那升腾起来的灰白色的烟气,以及被火苗吞噬被高温炙烤而逐渐卷曲的金纸,我思绪杂乱,似乎有很多的话要说,却又不知从哪里说起。
时间过得的确太快了,虽然母亲去世已经四十九天了,但是还依然觉得母亲的离世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依稀发生在昨天,就像母亲的五七,虽然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是过了14天了,但还是已然还像昨天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母亲的很多记忆也将逐渐变淡,生老病死是一个所有生命的自然规律,动物逃不掉,人类逃不掉,母亲逃不掉,你,我,他也同样逃不掉,虽然母亲去世这么久了,但是在我的心中还是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或者说是不想接受这个事实。
但是的确,母亲走了,家里空了,回家的理由变得牵强了,母亲这一词语已经变成了一种称谓,一种带着苦伤的甜蜜回忆但却是一种怅然若失的称谓,而这个母亲的称谓再也无法找得到具体的依托,母亲的称呼也成了一个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50年来,到现在我第一次感受到这种称谓变得如此的空洞,我是如此地一如迷路孩童般地茫然,亦是如此地毫不适应。
我知道 ,母亲的一切在这个世间已经无法用我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感受到了,而这逐渐流逝的时间也在说服我自己,接受这个现实,尽管它和我都是如此的执拗,彼此都在坚持,都在试图说服对方-----我只能在梦中与母亲相见了。相信母亲未曾走远,相信他日会曾相见,我亦是如此执着地坚持,我也无法预知我能坚持多久。但是,不管我是否承认,或者自己不去面对我的自欺欺人,我也早就认识到这个坚持就是一个失败,从母亲被推进火化炉的那一刻,从我在冰冷的骨灰收集室里面小心翼翼地捡着母亲的骨灰的那一刻,尽管那骨灰还带着最后的余温甚至还有些滚烫,但是那不是母亲的温度,只能是母亲假借火化炉让儿女感受到母亲的 最后一抹温热,从母亲的棺材被黄土遮盖住最后的那一抹红色的那一刻,就已然注定了失败。无法改变亦不可更迭。
佛教上讲,人去世的四十九天内死去的人是处于中阴身的状态,在此前,做超度最有效,打个不恰当的 比喻,在定罪之前贿赂管事的官员还是有效的,但是到了49天,就像人定了罪判了刑一样,根据生前的善恶业去轮回受报了,做超度虽然有效,但是效果是很有限的,我也是抓住这个时间,花了一定数量的钱请师父给母亲及母亲的冤亲债主做了超度,买油供灯,并且在七天内念了100部地藏经回向给母亲和母亲的冤亲债主。而我自己,除了日行一善,也抽空为母亲念了几部地藏经。
在此之前哥做了个梦,梦里面示现母亲的状况极其不好:在一个施工地点,母亲被人砍了头,哥跟那人说你要赔偿我们,那人说你还要赔偿,你要是再要赔偿,我就更加残忍地伤害你母亲,说完就用刀子划母亲的脸,血立刻出来了, 再有一个梦就是小外甥女做的梦,说是我父母状态还算可以,但是我父亲说吃不饱饭,一吃饭就有小鬼在哭,搞得父亲吃不下饭去,这两个梦警示着我们要为母亲做些什么,但是对于我,还没有做过关于母亲的什么梦,除了有一次梦见在老家父母坐在西屋的炕头那里,我看到母亲直知道母亲已经去世了,结果让我在现实中看到了母亲,我上前抱住母亲就哭,而母亲也那样地面无表情地任由我抱着哭。
《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中言 假使有人左肩担父,右肩担母,研皮至骨,穿骨至髓,绕须弥山,经百千劫,血流没踝,犹不能报父母深恩。对于我也是如此,生养之恩自不必说,单就我上初中和高补期间母亲为我起了三年的早,为我的求学之路准备了充足的底蕴和丰厚的资粮。
母恩难报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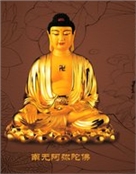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