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读书》杂志前,范用给人民出版社立了军令状
“现在看起来这是不是像天方夜谭,嗯?读书无禁区,这不是最起码的、ABC的东西么,居然有那么大的争论?”三联书店原总经理,67岁的董秀玉笑着说。30年前她曾亲身经历了《读书》杂志创刊和首篇文章《读书无禁区》掀起的狂风巨浪,深知这句话成为常识有多么不简单。
用今天的眼光看,不仅发表于1979年4月的《读书无禁区》是ABC,后来《读书》发表的《人的太阳必然升起》、《真理不是权力的奴仆》等一批文章讲的都不过是普通常识,然而董秀玉说在当年这些都是“心底的呐喊”,“之强烈和悲壮无与伦比”。中间还多次引发争论。《读书》的坚定,使杂志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风靡于知识分子中间,成为思想界的一面旗帜。
“在1979年,这样一篇文章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自问自答:“当时岂止是读书有禁区,中国刚刚解决了真理标准的讨论,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禁区尤其意识形态的禁区几乎全都没有破除,所以《读书无禁区》在特定时候所起的作用、面临的压力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
董秀玉承认当时几个主要领导者受到的压力,《读书无禁区》发表后,几位创办人都被严厉批评,勒令检讨。“四人帮刚刚倒了,但‘文革’的压力,疯狂到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下放了,几乎说错一个字就恨不得杀头。面对严酷的环境,这几个老人家刚从干校出来就开始密谋办杂志,倡导思想解放、独立思考,坚持真理,可那时还像搞地下工作一样。我从《读书》一开始筹备就跟着他们,强烈感觉到那时的氛围:忧虑、激奋、压力和斗志,是一种特悲壮的感觉。”
董秀玉说的“老人家”指的是“二陈一范”:陈原、陈翰伯和范用,以及《读书》的执行主编史枚、倪子明等老出版人、文化人。“《读书》杂志真是那些老人家创出来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扛着大旗往前奔,我们只是跟在后面跑。”那时董秀玉只是小辈,她说,她是“小跑腿的”。
1970年,被打成“陈范集团”的陈翰伯、陈原和范用在湖北咸宁干校谈起办刊物。范用回忆说:“我们设想一旦有条件,还是要办读书杂志。”“二陈一范”和史枚都是老革命,从三四十年代就开始办杂志做出版。1978年,时机终于成熟了。当时陈翰伯出任文化部新闻出版局代局长,陈原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范用则是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当时三联书店隶属人民出版社。
范用提出由他担任总经理的三联书店来办《读书》杂志,这是要担风险的:“人民出版社党组让我立了军令状:万一出了问题,责任全部由我一人承担。 ”1978年由陈翰伯出面,邀请于光远、夏衍、陈原、范用等人组成《读书》编委会。由陈原任主编,倪子明、冯亦代、史枚任副主编。
1978年下半年,37岁的董秀玉被从人民出版社编辑室抽调参与《读书》杂志筹备。“那时候条件很差,会都是在翰伯同志家里开;人很少,史枚坐在家里看稿审稿,我就负责在外面跑稿组稿。很多作者我不认识,老先生们就给我写封信或者帮我打个电话。”这样董秀玉联系到了巴金、萧乾、艾青、王蒙、黄裳、施蛰存等等老一辈文化人,以及一大批作者的热情支持,半年后编辑部逐步完善。
1979年4月《读书》创刊,在“编者的话”里声明:“我们这个刊物是以书为主题的思想评论刊物”:“我们主张改进文风,反对穿靴戴帽,反对空话,反对八股腔调,提倡实事求是,言之有物。”董秀玉回忆,当时老同志们的办刊思想就是要高举“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大旗,提倡人们多读书,独立思考,没有思想性的文章不要。陈翰伯就提出来文章要尖锐一点。陈原在讨论《读书》“刊物性格”时则说:“我以为办这个杂志,是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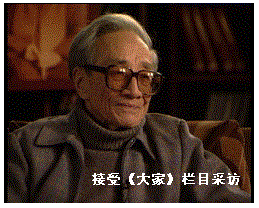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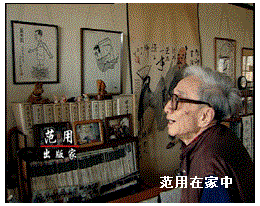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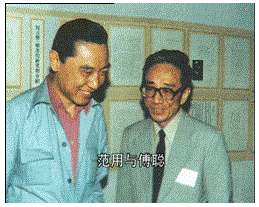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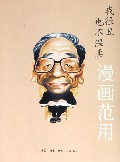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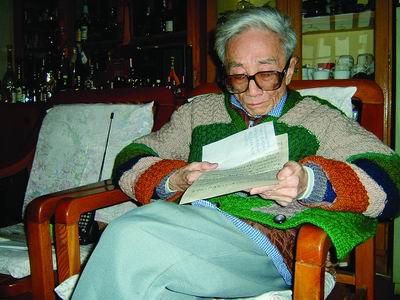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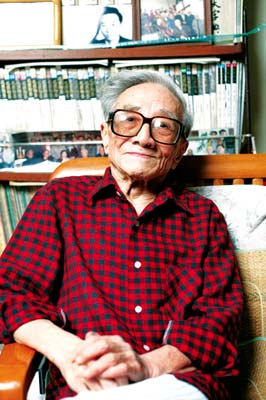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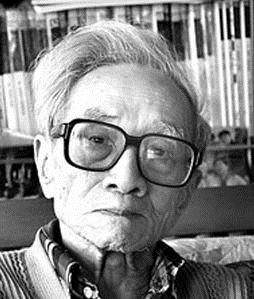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