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域记》的中国本位位思想及其影响
《大唐西域记》的中国本位位思想及其对两《唐书》的影响
自我本位(或中心)思想在各个国家、民族都是普遍存在的。例如,中国自古就有“华夷之辨”,其实质就是中国本位思想的存在表现。自认中国就是世界的政治和地理中心,故《诗经》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自认中国就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故《左传·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3],孟子也说:“吾闻用夏蛮夷者,未闻蛮于夷者也”[4]这些都是中国中心观的体现。中国自我本位思想在清朝还清晰可见,他们以“天朝上国”
自居,对世界的描述是“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5]可见自我本位思想在古代中国是普遍存在的。与完全脱离实际而盲目虚骄的夜郎自大不同,中国古代的自我本位思想基本与其始终为远东最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相称,其偏差之处只在于把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之一说成是世界的唯一中心。由玄奘口述,其门徒辩机录撰的《大唐西域记》自然也不例外。
首先,我们从书名就可以看出玄奘是把大唐看作天下的中心,放在第一位,而把他所经历的诸国都纳入了自汉代形成的中国之“西域”的范围。正如梁启超说:“吾国史家所称西域,不惟包含印度,乃至地中海四岸诸国,咸括于此名称之下。”[6]
与此书名相应的中国中心思想在《大唐西域记》内文随处可见。例如,该书的《序论》说:
我大唐御极则天,乘时握纪。一六合而光宅,四三皇而照临。玄化滂流,祥风遐扇。同乾坤之覆载,齐风雨之鼓润。与夫东夷入贡,西戎即叙。创业垂统,拔乱反正。固以跨越前王,囊括先代。同文共轨,至治神功,非载记无以赞大猷,非昭宣何以光盛业?玄奘辄随游至,举其风土。虽未考方辨俗,信已越五逾三。含生之畴,咸被凯泽;能言之类,莫不称功。越自天府,暨诸天竺,幽荒异俗,绝域殊邦,咸承正朔,俱沾声教。赞武功之绩,讽成口实;美文德之盛,郁为称首。详观载籍,所未尝闻;缅惟图谍,诚无与二。不有所叙,何记化洽?[7]
该书卷五还记载了玄奘会见中天竺的戒日王时的一段精彩对话:
戒日王劳苦已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对曰:“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王曰:
“尝闻摩诃至那国有秦王天子,少而灵鉴,长而神武。昔先代丧乱率土分崩,兵戈竞起,群生茶毒,而秦王天子早怀远略,兴大慈悲,拯济含识,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殊方异域,慕化称臣,氓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兹久矣。盛德之誉,诚有之乎?大唐国者,岂此是耶?”对曰“然。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昔未袭位,谓之秦王,今已承统,称曰天子。前代运终,群生无主,兵戈乱起残害生灵。秦王天纵含弘,心发慈愍,威风鼓扇,群凶殄灭,八方静谧,万国朝贡。爱育四生,敬崇三宝,薄赋敛,省刑罚,而国用有余,氓俗无穴。风猷大化,难以备举。”戒日王曰:“盛矣哉,彼土群生,福感圣主!”[8]
从以上两段引文可以看出,玄奘有随俗颂扬被东方各民族国家尊称为“天可汗”的唐太宗的意味,所谓“越自天府,暨诸天竺,幽荒异俗,绝域殊邦,咸承正朔,俱沾声教”之说等等,固然有些夸张失实,但是并非完全盲目的胡吹乱捧,而是与唐朝在当时的东方世界的国际中心的地位是基本相称的。至于玄奘与印度戒日王的对话,固然是当时没有人能查对和没有留下任何相关的旁证,后人也无从研究其真伪,但其在相当程度上真实反映了其时中印两国的国力盛衰强弱之差别,也是无可置疑的。
五代后晋刘晌撰的《旧唐书》有关天竺诸国的记载,并没有引用其玄奘会见中天竺的戒日王之部分内容,但反映了天竺诸国衰弱而遣使朝贡强大的唐朝的情况。其所记如下:
……贞观十五年,尸罗逸多自称摩伽陀王,遣使朝贡。太宗降玺书慰问。尸罗逸多大惊, 问诸国人曰:“自古曾有摩诃震旦使人至吾国乎?”皆曰:“未之有也。”乃膜拜而受诏书,因遣使朝贡。太宗以其地远,礼之甚厚。复遣卫尉丞李义表报使。尸罗逸多遣大臣郊迎,倾城邑以纵观,焚香夹道,逸多率其臣下东面拜受勃书。复遣使献火珠及郁金香、菩提树。
贞观十年,沙门玄奘至其国,将梵本经论六百余部而归。先是,遣右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天竺,其四天竺国王咸遣使朝贡。会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死,国中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立,乃尽发胡兵以拒玄策。玄策从骑三十人与胡御战,不敌,矢尽,悉被擒。胡并掠诸、国贡献之物,玄策乃挺身宵遁,走至吐蕃,发精锐一千二百人并泥婆罗国七千余骑以从玄策。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二国兵进至中天竺国城,连战三日,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阿罗那顺弃城而遁,师仁进擒获之,虏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头匹。
于是,天竺震惧,俘阿罗那顺以归。二十二年至京师,太宗大悦,命有司告宗庙,而谓群臣曰: “夫人耳目玩于声色,口鼻耽于臭味,此乃败德之源。若婆罗门不劫掠我使人,岂为俘虏耶?昔中山以贪宝取弊,蜀侯以金牛致灭,莫不由之。”拜玄策朝散大夫。是时,就其国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 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太宗深加敬礼,馆之于金飙门内,造延年之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延历岁月,药成,服竟不效,后放还本国。太宗之葬昭陵也,刻石像阿罗那顺之形列于玄阙之下。
五天竺所属之国数十,风俗物产略同。有伽没路国,其俗开东门以向日。王玄策至,其王发使贡以奇珍异物及地图。因请老子像及《道德经》。那揭陀国有醯罗城,中有重阁,藏佛顶骨及锡杖。贞观二十年遣使贡方物。天授二年,东天竺王摩罗枝摩、西天竺王尸罗逸多、南天竺王遮娄其拔罗婆、北天竺王娄其那那、中天竺王地婆西那并来朝献。[9]
而宋朝欧阳修、宋祁撰的《新唐书》有关天竺诸国的记载,则有引用玄奘会见中天竺的戒日王之部分内容,可见其对儒家所撰正史的影响与时俱增,实因其中国中心观符合儒家的天下思想传统。其所记如下:
……会唐浮屠玄奘至其国,尸罗逸多召见曰:“而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阵乐》,试为我言其为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祸乱,四夷宾服状。王喜,曰:
“我当东面朝之。” 贞观十五年, 自称摩伽陀王,遣使者上书。帝命云骑尉梁怀璥持节尉抚,尸罗逸多惊问国人:
“自古亦有摩诃震旦使者至吾国乎?”皆曰:“无有。”戎言中国为摩诃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诏书,戴之顶。复遣使者随入朝。诏卫尉丞李义表报之。大臣郊迎,倾都邑纵观,道上焚香。尸罗逸多率群臣东面受诏书。复献火珠、郁金、菩提树。……[10]
儒学史家的着眼点,毕竟重在世俗的军事政治之功效。故有关玄奘会见中天竺的戒日王之影响,只是作为唐朝在西域的世俗军事政治影响配合而提及。只有佛教本身的史家之著述,才会把玄奘作为中国文化在天竺诸国的传播者和征服者来记载。世俗与佛教界有关玄奘的传记,最终是把他由向印度取经求法者转变为代表中国向印度宣扬国威的宗教文化使者。例如,玄奘弟子辩机所写《大唐西域记赞》称颂玄奘云:
……骤移灰管,达于印度。宣国风于殊俗,喻大化于异域。亲承梵学,询谋哲人。宿疑则览文明发,奥旨则博问高才,启灵府而究理,廓神衷而体道,闻所未闻,得所未得,为道场之益友,诚法门之匠人者也。是知道风昭著,德行高明,学蕴三冬,声驰万里。印度学人,咸仰盛德,既曰经笥,亦称法将。[11]
又如唐道宣(596』67)所撰《续高僧传·玄奘传》云:
……初奘在印度声畅五天,称述支那人物为盛。戒日大王并菩提寺僧,思闻此国,为日久矣。但无信使,未可依凭。彼土常传,赡部一洲四王所治。东谓脂那,主人王也;西谓波斯,主宝王也;南谓印度,主象王也;北谓猃狁,主马王也。皆谓四国,藉斯以治,即因为言。奘既安达,恰述符同。戒日及僧,各遣中使赍诸经宝,远献东夏。是则天竺信命, 自奘而通,宣述皇猷之所致也。使既西返,又勃王玄策等二十余人,随往大夏。并赠绫帛千有余段,王及僧等,数各有差。并就菩提寺僧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俱到东夏。寻勃往越州,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自前代已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然后笔人乱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全言。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 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甑。尚贤吴魏所译诸文。但为西梵所重贵于文句,钩锁联类重沓。布在唐文,颇居繁复。故使缀工,专司此位。所以贯通词义,加度节之。铨本勒成,秘书缮写。于时驾返西京,奘乃表上并请序题。寻降手勃曰:“法师夙标高行,早出尘表。泛宝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辟法门。弘阐大猷,荡涤众累。是以慈云欲卷,舒之荫四空。慧日将昏,朗之照八极。舒朗之者,其惟法师乎?朕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敢仰测。请为经题,非已所闻。其新撰《西域传》者,当自披览。”及西使再返。又勃二十余人随往印度。前来国命,通议中书。勃以异域方言,务取符会。若非伊人,将论声教。故诸信命,并资于奘。乃为转唐言,依彼西梵。文词轻重,令彼读者尊崇东夏。寻又下勃,令翻老子五千文为梵言,以遗西域。……[12]
如此看来,“天竺信命,自奘而通,宣述皇猷之所致也”。而且其后的“前来国命,通议中书。勃以异域方言,务取符会。若非伊人,将论声教。故诸信命,并资于奘。乃为转唐言,依彼西梵。文词轻重,令彼读者尊崇东夏”。可见,中印通使及文化交流,在唐朝方面始终依靠忠于唐室而汉梵兼通的玄奘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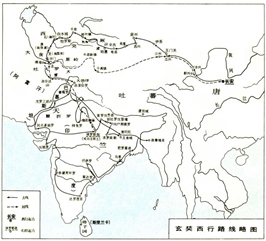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