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又是清明节了,父亲离开——已经是第六个年头。2002年的那个秋天,那个枯叶飘零的季节,父亲走完了不太长,却辛劳而顽强的一生,在家人的声嘶力竭地呼唤中永别了我们。还记得那个深秋的天空,灰蒙蒙的,整个世界变了颜色。秋雨纷飞,泪水纵横,宛如后山上针样的松树叶,在秋风中,一根根、一行行散落,铺了一地。每年的清明或父亲的祭日,每一个祭拜的日子,我都会想起父亲。对父亲那份深深的眷念,像是刻在了我的骨头里,无论在家乡的小城,还是在省会长沙,都刻骨铭心,越想越强烈。
父亲的病来得很突然,以至于一家人都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七年前的“五一”假期,几个同事约我一起在衡山观光。衡山是佛教胜地,其名远扬。我虽不信佛,但既来到衡山,我还是在衡山脚下,在祝融峰顶,同众多虔诚的信徒一样,鞠躬作揖,替自己和家人许下愿望,这当中就包括祈求上苍保佑一家人的健康平安。然而,命运有时就是样开玩笑。祈福的当晚姐姐发来传呼,说父亲胃痛要我回去陪父亲做检查。老家离城里并不算远,父亲到城里却不多。除了每年春节给在城里的伯父拜年,父亲难得到几趟城里。父亲的身体一直都很好,最冷的冬天也不穿袜子,很少患感冒,更从未见吃药打针。这次要到城里看病,我心里有一丝不祥之感。回到家里,我第一次细细的看父亲,父亲依旧穿着那件二哥穿旧了的兰色中山装,头上明显多了些斑斑白发,向来深邃的眼睛带着忧郁,古铜色的脸庞露出疲惫。父亲从未这般疲倦过,哪怕是从十多里的镇上挑百来斤的重担回家,父亲都没有这么精神不振的。这让我十分心酸,只叫了一声“爸爸”眼泪差点掉了下来。父亲的病要照胃镜。父亲躺在病床上,我拽着父亲的手,这也许是我记事起第一次这样紧紧地拽着父亲的手。父亲手上的厚茧,厚得让我难以想象,又粗又硬的,像儿时做游戏时用来做盾牌的樟树皮。
父亲就这样病了。病得这么突然,这么重,挽回的机会都不给,我认定这是上苍的不公。父亲任劳任怨、含辛茹苦,风里来雨里去几十年,好不容易将我们兄妹四人抚养成人、供我们上学、先后帮助二个哥哥和姐姐成家,凑钱帮我在城里买房……不谈享福,甚至还未来得及好好歇息一下,就这样被病魔击倒。为了不增加父亲的心理负担,我们瞒着父亲,说只是一般的胃病,养一段时间很快就会好。父亲是个老实人,没读过什么书,从未骗过别人,也深信自己的儿女不会骗他。跟人聊天,他告诉人家自己“得的是一般的胃病,过些日子就会好”,人家也会友善地回应说“胃病急不得,要慢慢养”。父亲天天在盼望早一点好起来,他有太多的事要去做,他什么都放不下。在城里养病的日子,下雨时他会说“雨下这么大,屋后的水沟好久没修了”,天晴时他又说“田里的稗子等着要扯”“你妈一个人忙不过来”等等,总是拗着要回农村。为了早点好起来,只要听见别人说哪种药吃了对胃病有好处,一生都舍不得花钱的父亲会急着要我们去买。为了不让父亲起疑心,我们也常常尽量满足父亲的要求,中药、西药和草药等只要能买得到的基本上都买了。农忙的季节,父亲的病情稍稍稳定了些,他以为自己恢复了。一天,避着我们去镇上挑回一担西瓜来,说是给我们口渴时吃。自那以后,父亲的病情越来越差。随着病情的不断加重,父亲的话也更少了,常常一个人躺在床上默不作声。有人来看他,他话也不多,说得最多的是“你太看得起了,这大老远的来看我”,说完眼角处会有一些别人难以察觉到的眼泪。后来,父亲还是怀疑自己的病来,偶而会跟母亲说,“还是要去医院看看,老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对父亲这样的要求,我们心里难受至极,眼看着自己的父亲这样耗尽生命,却无能无力。当初,我们就问过医生,由于是晚期,手术治疗风险很大,成功率极低,并建议保守治疗。当初,在我们拿不定主意时,父亲坚决反对动手术,可能当时是担心花钱的原故。父亲提出要去住院时,距父亲的病被确诊已有一年多,早已跨过了医生判定的期限,事后证明,医生的话是正确的,保守加保密延长了父亲的生命。越到后来,父亲想去住院治疗的心愿就更加强烈,我们做儿女的心也更加难受。后来,母亲说:“还是告诉他吧。”也只好告诉父亲了,我们不能再继续瞒下去,不然,就是罪孽深重。
后来,住在城里的三伯父回来看父亲,哽咽着将病情全部告诉了父亲。父亲只是静静的听着,一言不发。三伯父说:“你不要怪他们啊,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所以没有那么早告诉你,是怕你担心啊。医生说了,这种病,如果自己不清楚反倒会好些……”父亲一边听伯父说话,一边流着眼泪。最后,父亲说:“我不是怪他们,而是我没想到啊……我其他的倒没有什么,只是还有一些心愿不未了……”父亲的声音很低沉,伯父凑上前去问父亲是什么心愿,父亲停了停,慢慢地告诉伯父:“老二还欠着帐,女仔还没买房,我还没看见绍国娶亲没有看见他‘当官’啊……”这是父亲最后的心愿,跟三伯父说过这次话以后,就再也没说过稍长的话语,不再主动吃药,不再提去医院,甚至也很少跟母亲说话了。父亲一定还有千言万语要说,可是,他选择了沉默。从父亲知道自己的病情,到二OO二年十月十七日(农历九月十二)去世只有三天时间。
每每想起父亲最后的心愿,我都会泪流满面。父亲是个顾大局的人,为了大家庭的团结,父亲总是迁就忍让。甚至对兄弟邻里的一些无理要求,他都会主动让步,此后还会跟母亲说,“都是一个屋里,吵起来不好听”。父亲性格耿直,讲话讲理,为此还得罪过自己的亲弟兄。母亲曾经告诉我,有一次为了引水灌溉,父亲讲了一个伯父的直话,挨了伯父的一耳光,回家后没有说,后来在一次醉酒后才告诉母亲。为了子女的幸福,父亲一直忙碌奔波而勤俭节约。为了为我们准备学费,从我记事起,每年的春节,父亲都要做种苗生意。正月初五、六开始到邻市的种苗场买进梨、桃、柑、橙等水果种苗,每次都会买一大担回家。然后,徒步挑往普利桥、芦洪市以及花桥等附近(最近的有六公里)的圩场叫卖。父亲常常是早出晚归,每天凌晨六点吃一碗前晚的炒剩饭,中午则在圩场买二个面包充饥,如果回家早会再吃一些母亲留着的饭菜,晚了便是二餐作一餐。母亲常常叮嘱父亲,饿了要记得在街上吃盒饭或者米粉,可是父亲总啥不得,反过来还时常反问母亲:“我一担种苗一共才赚得几块钱到?”每年都这样,年复一年,直到得病的那一年,父亲告诉母亲,“今年卖种苗赚了六百多”。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心里只有儿女,没有自己;只有爱,没有恨。四兄妹中,父亲是最喜欢我的,虽然平时没有表露出来,但从他一言一行中都可以感觉到。不仅因为四姊妹中只有我一人考上了学校,而且还进了政府机关工作,我是父亲的骄傲。在父亲朴素的世界里,以为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人都是可以做官的,以为只要能管住几个人,便是官。以至于,每次回家,父亲都免不了要告诫我好好努力,好好工作,争取早日当个“官”。二00二年十一月,也就是在父亲去世半个月后,通过公开竞争,我当上了民政局的办公室主任。那天夜里,我梦见父亲在天堂里笑。梦醒后,我却泪湿枕巾——父亲对我如此期望,我却只能在梦里与他分享。
父亲的每一个祭日,无论在家乡小城,还是省会长沙;无论是父亲坟前,还是上班路上,我都会想起父亲最后的心愿,并将此作为对自己的最好的激励和最重的鞭策,一直努力,不断奋进。而且,每每实现一个愿望,我都会来到父亲的坟前,烧一把冥钱,斟三杯米酒,磕三个响头,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天上人间,我都会永远是他的骄傲。
怀念父亲,怀念他给了我生命;怀念父亲,怀念他教会了我做人;怀念父亲,是为告慰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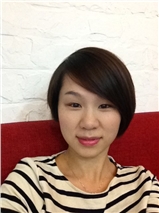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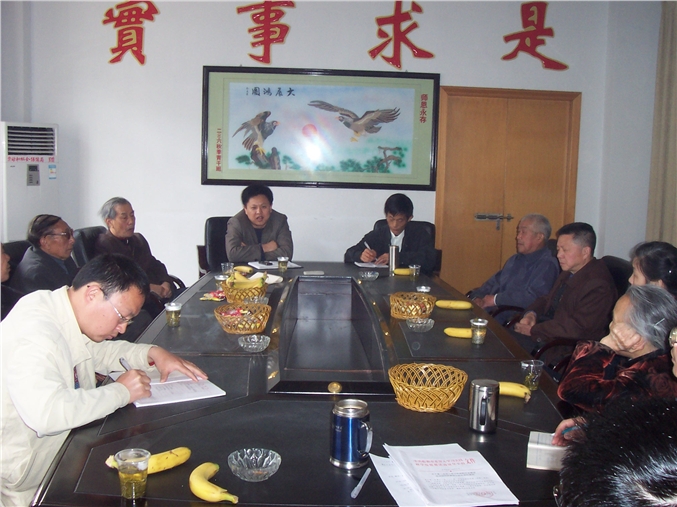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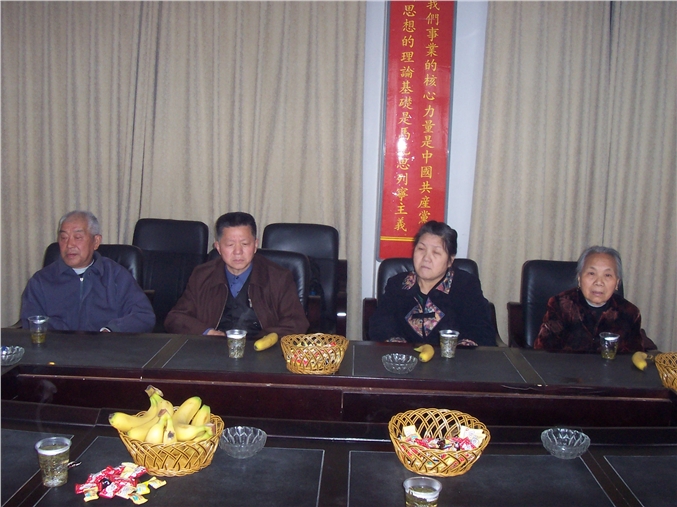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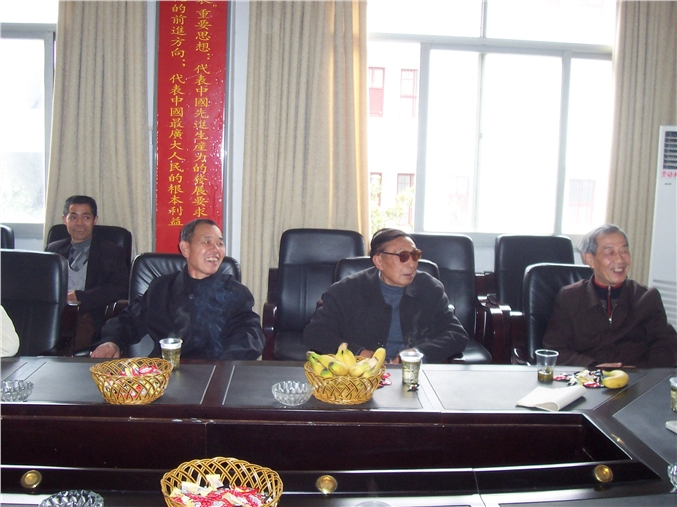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