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主要的憲法學思想
首先要說明的一點是,這裏所稱的“憲法學思想”與上文憲法學家的第三個標準中所指的憲法學思想略有不同。這裏主要是指梁啟超對憲法學的研究及其思想。
(一)論憲法和制憲權
憲法是什麽?這是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梁啟超認為,“憲法者,英語為Constitution,其義蓋謂可為國家一切法律根本之大典也。”“近日政治家之通稱,惟有議院之國所定之國典乃稱為憲法。” “夫憲法者,國家之根本大法也。”又言,“憲法者何物也?立萬世不易之憲典,而一國之人,無論為君主為官吏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為國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後無論出何令,更何法,百變而不許離其宗者也。”“憲法之職任,在予政治以永久可循之常軌。
梁啟超認為,各立憲政體國家憲法雖有差異,但大體均有政體、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國會的權力及選舉議員的權利、君主及大統領之制與其權力、法律命令及預算、臣民的權利義務、政府大臣的責任等內容。憲法有成典憲法與不典憲法之分。成典憲法、不典憲法“舊稱成文憲法、不文憲法,用語不愜。如彼英國之憲法固有文字非恃口碑也”。成典憲法之中,有硬性憲法,有軟性憲法。]梁氏認為,“立憲政治之信條”,其一由於憲法;其二由於政治上之習慣而生。“憲法則有形之信條也。政治上習慣,則無形之信條也。是故凡立憲國民之活動於政界也,其第一義,須確認憲法,共信憲法為神聖不可侵犯。雖君主猶不敢為違憲之舉動。國中無論何人,其有違憲者,盡人得而誅之也。其第二義,則或憲法未嘗有明文規定者,或雖有規定,而中含疑義,可容解釋之余地者,或雖無疑義,而當其行使此權利,有可容伸縮之余地者,凡此則皆由政治上之習慣,積累而醞釀之。醞釀既熟,則亦深入人心而莫之敢犯。”憲法與政治上之習慣,“兩者之效力相等。而無形者之宰制人心,時或視有形者更為甚。以立憲政治之信條論之,則憲法與政治習慣,叠相生而叠相成。兩者和合,自產出種種條件,而畫然以示異於非立憲之政。”按照現在的理解,梁氏所謂政治上之習慣大致相當於憲法慣例。梁氏對憲法慣例的適用情形、效力、以及其與憲法之間的關系的論述可謂十分精辟而獨到。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梁啟超在行文之中對違憲與違法還作出了區分。例如,梁氏認為,立憲國政治上的詔旨所易引起的責任有三種:第一,違憲責任;第二,違法責任;第三,失政責任。違憲與違法的不同是因憲法與法律的地位不同而引起的。當然,梁氏並未就此展開論述。
制憲權歸屬於誰,這是憲法學的一個重要命題。梁啟超的認識也是十分深刻。梁氏認為,“就法理上論,主權在國民全體,明載於臨時約法(即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引者註),(國民-引者註)自動制憲,即此主權作用之發動,最為合理。”為防止政府與國會勾結盜取民意,敗壞國事,禍害國民,必須求諸憲法。“憲法如何而始能予我以此憑藉?舍國民自動制憲外,其道末由。”所謂國民制憲,即“以國民動議(Initiative)的方式得由有公權之人民若幹萬人以上之連署提出憲法草案,以國民公決(Referendum)的方式,由國民全體投票通過而制定之”。國民制憲為國民自衛的第一義。
制憲權為何不可畀諸國會?梁啟超認為,“蓋憲法者,所以規定國家各機關之權限,其不容由一機關專擅制定,理本甚明。”先有憲法,然後有選舉法,然後才有國會。而且,“制憲權本非國會所宜有。”他認為,臨時約法以此權委諸國會,實為憲法難產的一最大根源。“臨時約法所以將此權畀諸國會者,實緣受‘國會萬能’之舊觀念所束縛。”
關於國民制憲,有人主張召集國民大會。梁啟超認為其意甚美,但國民大會主要事業應為制憲,且應由國民動議或國民投票兩種形式組織。[15]並認為若議員成為其成員,則應“以國民會議議員之資格制憲法,非以國會議員之資格制憲法”。在修改憲法之時,應由“國民特會”這一超乎立法行政司法三機關之上而總攬主權的最高機關。當然,“國民特會”只是行使主權的行使者而已,國民全體為主權的所有者。
(二)論憲法的精神
梁啟超認為,憲法有三大精神。他對此的理解可謂深悟憲法的精髓。
1.國權與民權調和
梁啟超認為,一個完全至善的國家,“必以明政府與人民之權限為第一義。”“使人民之權無限,其弊也,陷於無政府黨,率國民而復歸於野蠻。”“使政府之權無限,其弊也,陷於專制主義,困國民永不得進於文明。”國權與民權的消長,反映於政治現象上即為幹涉主義與放任主義的辯爭。雖然說,國權與民權不可有所偏畸,但各國制憲者自當審視其國情,“或因本能之所長而發揮之,或因積習之所倚而矯正之,要不外以損益之宜,寓調和之意。”中國應如何損益調和呢?特重民權主義者認為,我國數千年困於專制,“非采廣漠之民權主義,無以新天下之氣。”特重國權主義者認為,我國雖號稱專制,但實際上以放任為政。現今應以廣漠的權限委諸國家機關,整齊嚴肅國務,鍛煉國民,以求競勝於外。梁啟超則認為,極端的民權說和極端的國權說皆不可取。當日中國“民權之論,洋洋盈耳,誠不憂其夭閼,所患者,甚囂塵上,鈍國權之作用,不獲整齊於內競勝於外耳。故在今日,稍畸重國權主義以濟民權主義之窮,此憲法所宜采之精神一也。”當然,梁啟超的這種認識與其對放任與幹涉的認識是相關的(待後文述之)。
2.立法權與行政權調和
梁啟超認為,孟德斯鳩倡導三權分立,國會的立法權與政府的行政權各安其分,互不侵越。然而,征諸各國經驗,孟氏之說難以成立。國會行使的不僅是立法權,而立法權又未能專屬於國會。國家分設國會與政府,本欲使之互相限制而各全其用。如果“行政部中人全由立法部之多數黨出,國會與政府純為一氣。國會所謂監督者,盡成虛語。茍政黨之道德不完,則陷於一黨專制之弊。”如果“政府對於國會,緣畏憚而生佞媚,緣娼嫉而思操縱,全用籠絡離間之術,使議員各自暌渙以入吾彀,而國會亦終成為政府利用之具。”“各國所以調和此兩權之法,大率各因國情積經驗以成良習。”“國家之所以設國會,實欲假途於此以求得一理想的政府而已。所謂理想的政府,其條件有二,一曰善良,二曰強固。何謂善良,常兢兢焉思所以龔行國家之天職,斯善良矣。何謂強固,其力實足以龔行國家之天職而無所撓敗,斯強固矣。”梁氏認為,“國家之行為何?行政是已。國家之意誌何?立法是已。”“政府譬則發動機。國會譬則制動機。有發而無制,固不可也。緣制而不能發,尤不可也。調和之妙,存乎其人矣。”
3.中央權與地方權調和
中央與地方關系一直是中國憲法、中國憲法學的一大難點。梁啟超認為,中國憲政的最大問題,就是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程度。“無論何國之政治,斷未有能為絕對的集權者,亦斷未有能絕對的分權者。然程度之或毗於此,或畸於彼,則緣國情而各有所宜。”梁氏認為,“畸於分權者,宜以勿妨害國家之統一為界;畸於集權者,宜以勿犧牲局部之利益為界。為不越此界者,則其政皆可雲善良。而在幅員狹、交通便之國,則以稍畸於集權為宜;在幅員大、交通艱之國,則以稍畸於分權為適。此其大較也。”中央權與地方權如何調和,梁氏認為,中國因為歷史上的關系和地理上的關系而不得不暫畸於分權。從自然界的現象來說,中國“地理遼遠,鞭長莫及,雖欲集權於中而有所不能,斯固然矣。”而從政治現象來說,“我國而欲行畸於集權之政,匪惟有所不能,抑亦有所不可。”“我以四千余萬方裏之地,能宰制於一中央政府之下,誠足以自豪,然政治之馳而不張、疏而不備,國民特長之不能發揮,幸福之不能增進,弊亦未始不坐是。”立法權、行政權均不可盡集中於中央。等到交通之便大開,方能由分權以趨歸於集權。梁氏指出,“中央議會與地方議會權限之大小,當視中央行政機關與地方行政機關權限之大小為比例是也。” 即所謂“監督機關權限之大小應與執行機關權力之大小成比例。”“其在行集權制之國,則監督權亦集於中央而已足;其在行分權制之國,則監督權亦不可不分於地方。” 其時,梁氏主張的綱要是:“各省置總督或巡撫為行政機關,於國法所委任置範圍內有處理一省政務之全權,惟對於省議會而負責任。各省置議會為立法及監督機關,於不背觸國法之範圍內得決議其一省適用之法律,且對於督撫而有上奏彈劾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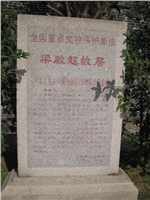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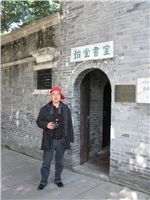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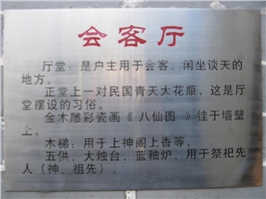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