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倏然消逝”的思考(转)
【转自:丽子的BLOG 2007.12.07 20:33:00】
今天在 MR Luo的课上惊闻人大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生导师余虹跳楼身亡。回来之后上网一看,相关的报道已是铺天盖地。我打开了余老师的博客。他的博客创建于07年8月9日,距他自杀的今天还不足三个月。我想,余老师的轻生绝对不是一时的念头所促的,三个月前也许他就已经默默地决定好在人世间留下自己最后的公开的文字,在这个虚拟的空间中留下关于死亡的讯息。在他07年9月13日的博客文章《一个人的百年》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余老师选择了高空坠落,像一片落叶,拥抱他所向往的尊严与勇气的另一极。文人自杀往往让人无法正视,无法言语。或许,尘世有太多的浮杂让其厌倦,天堂的那一边有着他所追寻的终极救赎。他是否能在彼岸世界获得解脱,我们无法证实,但作为生者只能寄予祝福:余老师一路走好。
其实,之前我并不认识余虹教授,牵动我心的是他的中文系学者身份,因为这让我又想起了本科期间两次印象深刻的学生自杀事件。
一次是2005年4月北大03级一名文学院学生自杀。和我们同年级同专业,自然带给我们很大的心理震撼。还记得当时宿舍同学一起看了这位女生临死前在未名BBS上的遗言都唏嘘不已:“我列出一张单子,左边写着活下去的理由,右边写着离开世界的理由。我在右边写了很多很多,却发现左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写的……对于亲人,我只能够无奈,或许死后的寂静,就是为了屏蔽他们的哭声,就是能让人不会在那一刻后悔。”生和死的理由被放置在左右手做最简单的计算和比较,这种“举重若轻”的怪异感让人心悸。在那之后,我多次去过北大,每次经过逸夫苑理科楼时,总是会想像着这个遇到生存困境的女孩是如何在这里徘徊在生命的边缘。或许犹豫再三,或许没有过多的挣扎,最后的抉择都是飘然落下,可是当她听到自己落地声音的那一刻,是否真的丝毫没有后悔?
另一次是07年5月北师大艺术传媒学院影视系研三学生孙莹洁跳楼事件,她本科也是中文系学生。孙师姐的跳楼在本校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时蛋蛋网中有着各种各样的悼念和评说文章,今天蛋蛋不巧正在整修,暂时关闭了,所以我很难找到原文。但是记忆中,有许多认识孙师姐的同学写了悲痛的悼念文章,在他们眼中,孙师姐善良,温柔,聪颖,有才华,他们都无法相信一位如此优秀的同学竟然在毕业前选择离开这个世界。也许正如她的一个同学所说,她的香消玉殒是因为她太完美主义了,容不得一点瑕疵。但是,现实生活中总有太多的不如意,当完美主义心态遭受生活的打击而七零八落之时,离开便成为最后的选择。
这些中文学子的离开让我的内心无法平静,也许在他们眼中,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死亡并没有那么可怕;也许,死亡也是一种美丽的结束。甚或,知识分子的死亡是对自己理想的终极逾越。就像尼采、叔本华、王国维、老舍等等,当社会的现实给个人的精神世界带来深深的绝望而不可挣脱之时,苟且活着便是对理想和生命的亵渎。思考者是最痛苦的,当一个人深入了解世界的本质和真相时,他就开始愈加孤独,愈加痛苦,不可超脱。
然而,在这些自杀事件中,我的关注视角总在这些死者的身边,那些爱着和关心着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我总是无法想象,当这些绝望的人想到身边还有那些关心和在乎自己的亲人时,他们是如何有勇气做出离开的决定?当我得知余虹老师死前处于单身阶段时,我似乎能稍微理解一些。这并非说婚姻和家庭的不幸导致他的自杀,而是说没有家庭的牵挂,他的自杀决定能够比别人轻松。而北大中文系和北师中文系的两位同学,她们又是如何能够在纵深跳下之前屏蔽了爱她们的亲人的呼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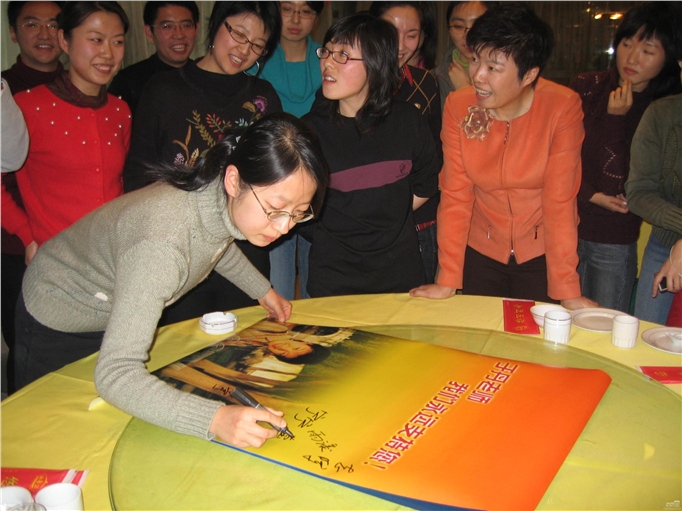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