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峙立(山东画报出版社)
总以为我们有的是时间。
总以为来日方长。
总以为“时日无多”这个词很遥远很空幻。
董先生走了。我深爱的董治安先生,我尊敬的老师,离开我们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述心中痛楚。
大归,往生,远行,西游,这些字,没有一个是我愿意用在董先生这里的。汉语中有一个词“音容宛在”,我们也常常用这个词来表示思念之情,可是,“宛在”竟是“不在”,宛在,是更痛,是更伤怀。
可我记得的,关于董先生最后的画面,是温暖舒适的。
五一长假的一天,众弟子陪董先生钱先生郊外出游,春末夏初,山青水绿,杂花满树,是好时节。午后,董先生在水边钓鱼,钱先生坐在一旁,董先生闲闲地讲他高中毕业的那年,也是在水边,也是钓鱼,是真的野外垂钓,先用小米撒在水面上,这叫“做窝”,意思是告诉鱼儿此处有食儿快来啊,然后将蚯蚓鱼钩甩过去,诱惑水中鱼。
我也照葫芦画瓢广撒鱼食儿,做窝,甩钩儿,起杆,一条鱼也没有钓到。董老师钓到大鱼,我们拍掌欢笑。董老师叫我过去,说徐峙立你到我这来钓,我有点累了,到车上歇歇。
我不知道为什么,董老师走后我经常会想到这一幕,每次回想都以这句话终结,泪流满面。
我爱董先生。我知道我在学术方面未能学得先生万一,常生愧意,悔不该当初不好好念书。我在学校跟从先生读书的时候,不求甚解,不思进取,反而热衷于电影娱乐新闻媒体。先生生不生气我不知道,但是先生未曾因此责备我。因材施教,也正是这样的吧。先生帮我们打下人生的基石,教我们处世做学问之道,顺我们自己的心性发展。
我曾经央求董老师写写回忆文章,让我们知道他和钱老师过去的日子,做学问也好,日常生活也好,朋友交往也好,那个时候是怎样过的呢?像是何兆武《上学记》,像是杨绛《我们仨》。董老师坐在沙发上眯眼乐了:嗬,约稿约到老师这里来了。闲闲地讲往事给我们听:那个时候都在不同地点下乡,不能互相照顾,估计着钱老师要生了,他跟老乡买了小米和鸡蛋,背在身上,走了几十里地赶过去。讲完还笑笑说,是真正的土鸡蛋。
说完他又不着急写,他有更重要的工作,他要负责“两汉全书”,我也不催,时间长着呢,也许等老师年高之后再写写回忆录消磨时光吧。
登门看望董先生钱先生,我们常常一家三口一同前往,我想私心里我是希望董先生看到他的两个学生缔结的家庭幸福和美。偶尔小女念书上学不能同去,董先生站在门口一脸失望地问我:“大人物”怎么没来啊?我心里就有些小小愧疚,啊,他喜欢和孩子在一起,快乐无拘束,我让他们失望了。钱老师就把准备好的巧克力糖塞到我手里,说,嗱,徐峙立你吃吧。小女会揉着先生的脸,说董爷爷你要多吃东西才能不长皱纹;小女会告诉钱奶奶那种绿色的艾草糕真好吃,奶奶给的高迪瓦牌子的巧克力济南买不到。我们没有做到这些,我们许是敬佩先生学养人品,反而不敢在先生面前流露自然态,我们总是周五郑王一本正经地问候先生,规规矩矩说话。
我很爱看到董老师和钱老师互相之间喊着对方的名字,同学一样,连名带姓地喊,觉得他们真的是亲密。钱老师从冰箱里取出一只青花瓷小碗,盛着蒸过的红枣,说是给董老师特意蒸的,请我们一起尝尝。小女在一旁笑:董门弟子,与有荣焉。
往事,都成追忆。
2009年9月,母亲离开我;2012年5月,董先生走了。三年时间,我失去两位最最亲爱的人。原本以为心如刀绞是个很夸张的词,经历之后,才发觉,有些人有些事,一想起来,心真的会疼,是钝刀割切的那种疼。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谈起他妈妈离开之后的伤感:就是,特别特别害怕一天天下去,时间会一点点毁灭妈妈曾在这里的证据。冰箱的牛奶,是妈妈送去医院的那天早晨买的,可是终究要喝掉;餐桌花瓶的那束花,是妈妈亲手插的,几天之后也会枯萎。最想要做的,就是记住。他把妈妈穿旗袍站在海边吹海风的照片挂在墙上,每日插放妈妈喜欢的鲜花,旁边摆着妈妈爱看的小说。
也许真的有两个平行世界,虽不再相见,但我们一直深爱对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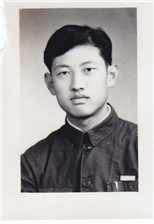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