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忆张总
张有天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有接近十年的时间,下个月初就是清明节了,我想在这个缅怀故人的节日之前,写一篇短文,通过我的一些回忆片段和印象,来寄托我对老人家的怀念和哀思。
张总,一位风度翩翩的老先生。我于2003年7月来水科院结构所结构二室(现名大坝与地下结构工程研究室)读博士研究生。来到之初,我的导师陈重华教授带我认识研究室和所里的同志,张总当时虽然任院副总工,但是很多时间仍在我们研究室内办公,那时我对张总有了第一印象——鹤发童颜、声如洪钟、身材高大,看起来器宇不凡。我对张总的这个印象,在别人眼里也是如此的。
2004年夏季,我在清华大学旁听上课,认识的一个研究生来找张总审阅论文,学生办完事下楼梯时很兴奋对我说:张先生好有风度。我想,张总的风度是源于内在的学识和修养。
张总,一位很有学问的专家。很遗憾,我和张总有接触的时间仅三年多,我当时还是一名学生,在科研方面还稚嫩,因此我不能深入地向张总请教问题、一起讨论问题、充分领会他博大精深的学问(我那时向张总请教的一些问题,在张总眼里应该是比较肤浅的,但张总还是耐心的给我解答)。我对张总学问的了解,更多的是从侧面知道的、从我研读他的论文和著作时理解到的。
我的导师陈老师在我的心目中很有学问(陈老师早年在清华大学毕业,在加拿大师从著名岩土力学专家摩根斯坦取得博士学位),但是,我有一天和陈老师讨论问题聊到了张总,陈老师对我说:张总学问大、名气大。
2004年,清华大学的李仲奎教授为我们讲授水工地下结构,李老师知道我在水科院结构所上学后,他是怀着很尊敬的语气说起张总的。
我从同事们那里,陆续地知道了关于张总的大学问和他在水工界的知名度等事情,同事们常常提起的:张总在某某国家重点工程的审查会上发表的建议如何、张总和潘家铮院士关于某某问题的讨论如何、等等;以及后来我亲见的,在张总的带领下室内同志取得大禹科技进步奖(此前,张总已获得很多科技奖励,其中包含国家科技进步二、三等奖)、张总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撰写专著《岩石力学与工程》、起草《水工隧洞设计规范》等事情,都反应了张总的大学问。如果没有大的学问,怎会做到这些?!
自我毕业留研究室工作,至今也快有十年时间,在这些年的工作中,我经常查阅张总当初主持科研项目的成果报告、他参加起草的行业规范、阅读他发表的论文和专著,越发感觉到了张总有大的学问和影响力。
我认为张总的大学问表现在:把他多年的工程经验和研究成果密切联系,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了棘手的工程问题;把他在岩石水力学、水工地下结构等方向的系列研究成果整合,提炼到了高度,系统化形成理论体系;他著书立说、发表高质量的论文,长期被业内引用。学问能做到张总这样好的,在科技工作者群体内已属不易,已是凤毛麟角。所以,我个人对张总的学问满怀憧憬,心向往之,也常常以张总为楷模勉励自己。但是,我清醒的认识到我的天分远在张总之下,且心气浮躁,我这辈子能获得学识和成绩估计与张总相去甚远。无论如何,看过和亲近过张总这座高山,我自己还是要勉励自己要积极工作、不要沦落。
张总,一位和善的老人。在生活上,和张总相处的日子不多,但是有些事情我会永远记得,张总是愿意帮助我这个晚辈的。我在上学时,觉得自己的工程概念不足,有一次研究室内做一个隧洞项目,张总打算去现场踏勘。我当时知道,我并非主要业务人员,能参加现场踏勘并非易事。所以,我请求张总:能否带我一起去看看现场、增长一下经验。张总立刻答应了,并且认真地向研究室和所里反应了我的愿望。后来,这次考察因故没有成行,张总和我都没有去。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感激张总,这位善良、乐于帮助和提携别人的老者。
在我毕业答辩之前,毕业论文需要多位专家审查,因为答辩期间时间紧张,我不得不在晚上9点多送论文到张总家,打扰了他的休息时间,张总仍然和颜悦色把我让到房子内,向我询问论文的基本情况。大概过了两、三天的时间,张总看完了我的论文,给我认真地写了意见和建议,让我感到温情和关爱。
张总在2006年国庆假期的前一天猝然离世,我当时刚回到老家探望父母,凤鸣老人知道了这种情况,担心我心里着急,所以当时她没让人通知我张总去世的消息。当假期结束,我回到北京上班,陈平老师黯然神伤地告诉我张总走了时,我感到震惊和悲痛。
在张总逝世前大概半年,我看见他在家属区散步,步履已现沉重,望着张总的离开的背影,我心里很是伤感,我今天仍然能回想起我当时的那种心情。今天,张总离我们而去即将十年,让我用这段文字来表达我对老人家的崇敬、感谢和怀念,希望生者坚强,同张总的家人和生前好友共勉一声:保重!也希望张总带领过的我们这个科研团队持续发展,希望张总开创的科研理论发扬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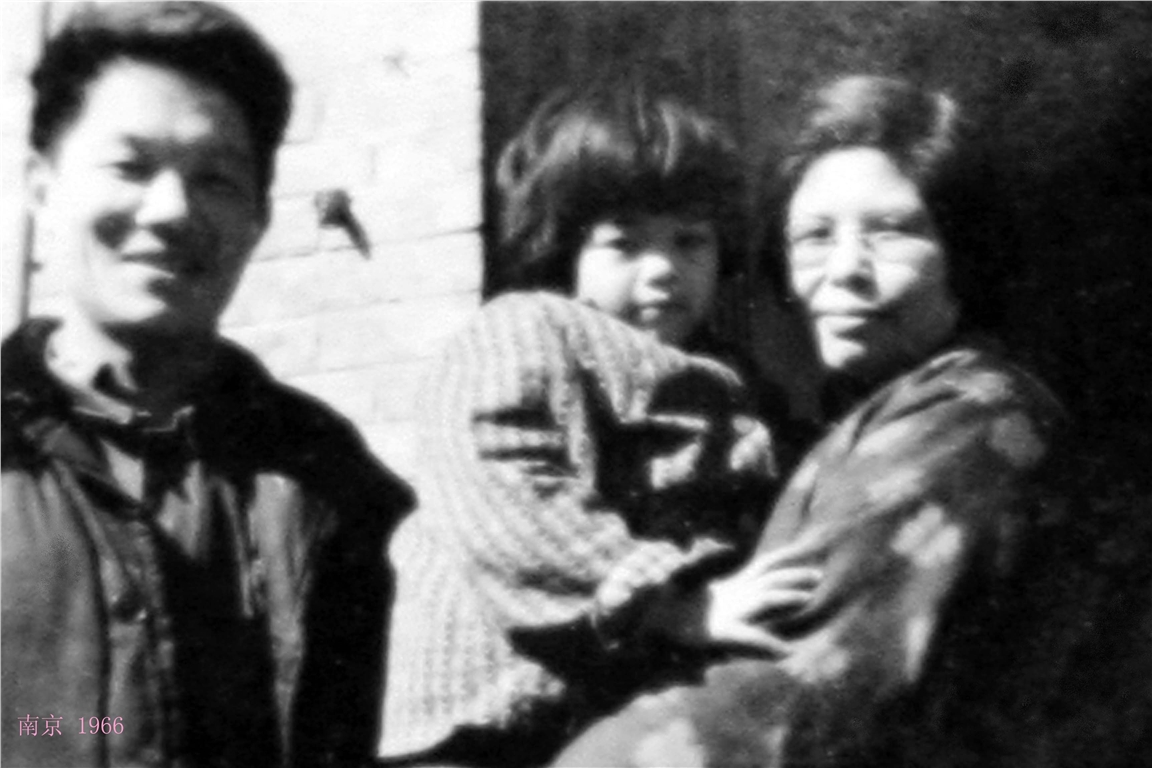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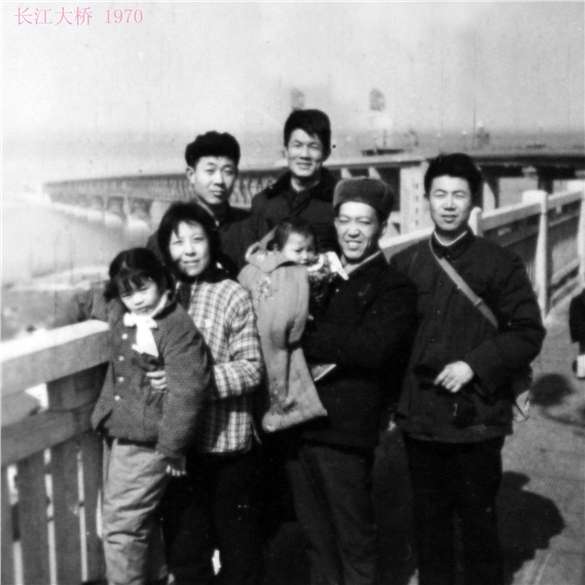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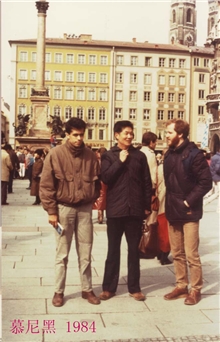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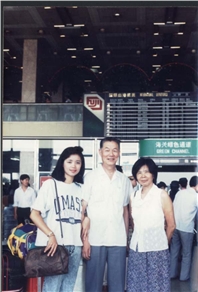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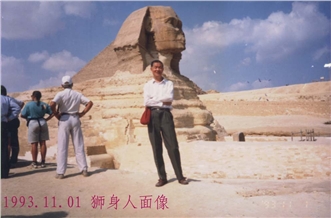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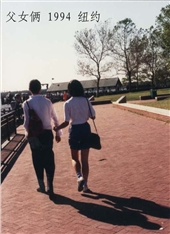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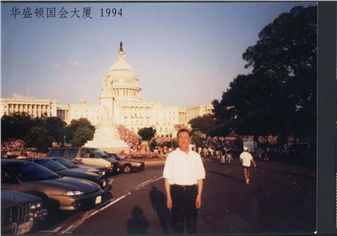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