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缅怀王益同志
深受我尊崇的老出版家王益同志,走完了他92年的光辉历程,告别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和跟着他脚步前行的人们。作为他的老部下和他的事业的继任者,我更想由悲痛转化为思念。
从1935年参加生活书店到因病重不能理事,王益同志为出版事业不曾间断地操劳了70多年。他一生只做了出版这一行,而出版的各个主要方面他都工作过。他长期从事图书发行工作,也做过编辑出版和书刊印刷工作。他主持过人民出版社和新华书店总店的工作,更长期在国家出版管理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像王益同志这样做出版工作时间之长、任职范围之广、积累经验之丰富,因而对出版事业贡献方面之多,在我国出版界是罕见的。
王益同志对出版事业的贡献和他的思想品格,常常使我产生敬佩之情。王益同志在解放前,对革命出版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后又是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开创者之一。在这里,我主要讲讲近30年来的一些感受。
对振兴中国当代印刷的重要贡献
王益同志对发展我国印刷事业的贡献,应当以浓重的笔墨写入当代中国出版史册。在已出版的以《不倦地追求》命名的三本王益著作中,仅专论印刷的就有76篇,涉及中国印刷的历史与现状,中国印刷的技术改造、体制改革、经营管理、人才培养,中国印刷史学研究和博物馆建设,中国印刷对外交流与合作以及对外国印刷业的考察、中外印刷比较研究等,印刷业的方方面面无不倾注着王益同志的心血和智慧,振兴印刷、发展印刷,成为王益同志不倦的追求。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是我们祖先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到了近现代,特别是到了需要加快发展出版事业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才痛切地感受到被西方发达国家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印刷技术和装备严重落后,印刷生产能力严重不足,造成出书慢、出报难,出版周期长,压得出版部门各级领导喘不过气来,成为当时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永恒主题”。王益同志经过认真调研和周密思考,于1982年8月7日在新华社《内参》上指出:“不尽快地用新式的机器和新的工艺来取代陈旧的老式设备和落后工艺,是很难改变书刊出版这种落后状况的。”“目前由使用单位进行研究的办法要改变。”他建议由国家经委牵头,“机械、轻工、化工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搞好印刷技术改造”。这项建议得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完全赞成”,在写给时任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并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的信中指出:“为了解决我国出版事业的极端落后状况,非请机械、轻工、化工三部门大力协作攻关不可。此事希望中宣部和经委共同牵头来解决。”从中央采纳王益同志的建议起,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机,关注和解决出版印刷落后问题,不再局限于使用单位和宣传、文化部门,而是提到党和国家最高当局,成为国务院领导下各有关部委共同谋划和实施的国家技术改造专项,并经十余年的协作攻关,我国印刷由手工铅排到激光照排、由铅版印刷到胶印印刷、由照像制版到电子分色、由单机装订到联动装订的全面性历史飞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印刷技术严重落后的面貌,为我国出版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在为《亲历出版三十年》撰写《印刷技术革命的历程及其历史性巨变》一文时,我深情地回顾道:“我个人有一种非常幸运的感受,在我担任新闻出版署主要领导职务的时候,再也没有当年徐光霄、王匡、陈翰伯那种沉重压力了,新闻出版署主管印刷的机构,再也不会像20多年前那样做着全国印刷生产总调度室的工作,而是侧重于对我国印刷技术、印刷工艺和印刷企业管理如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筹划。人类印刷技术的发展,从铅与火到光与电是一个历史性的飞跃;现在又有了新飞跃,进入了0与1(数字化),或者可以说是光与电、0与1相结合的新时代。技术的革新与进步永无止境。抚今追昔,请允许我以中国出版界受益者的名义,对提出应由国家经委牵头组织联合攻关建议的王益同志,向领导、主持、参与其事的其他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与敬意。”
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首创者和奠基人
我国出版改革是从发行体制改革起步的,而发行改革则是由王益同志提出并组织实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拨乱反正,我国出版事业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图书品种和印数迅速增长,广大城乡读者对图书需求更是与日俱增,出现了社会普遍关注、反映强烈的出书难、买书难问题。这首先是由于印刷落后、出版周期过长的原因造成的,而发行体制存在弊端使流通不畅也是重要原因。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实行专业分工,出版社集中精力搞编辑出版,图书发行由新华书店独家经营。这种体制有其历史积极作用,但流通渠道太少、购销形式和所有制形式单一,出版社不得自办批发,开办个体、集体书店也受到限制,已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疏通流通渠道,搞活发行体制,增强发行能力,迫在眉睫。
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王益同志早在1982年即提出:“以国营书店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一主三多一少”)的改革思路,并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1983年作出的《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对主渠道的改革、出版社的自办发行、多种购销形式的出现和民营书业的发展,都起到了推动作用。1984年,王益同志又提出,从改变出版与发行绝对分工、出版社也要搞发行入手,推动包销改为寄销,适当提高书价,出版社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化,对图书出版与发行的传统体制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新思路。王益同志的意见在新华社《内参》发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于同年11月8日写信给邓力群并中宣部出版局、文化部出版局,说“王益同志所提意见,触及了现行出版发行制度弊端的症结所在,这是建国以来没有人提出过的”。王益同志积极倡导和组织实施的出版发行体制改革,既缓解了当时困扰出版界和广大读者的“买书难”,又为日后的深入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出版事业不倦追求的智者与行家
从1959年起,因同住文化部宿舍的一个楼层,我开始认识时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长的王益同志,感到他知识渊博而又平易近人。1972年,他和我先后从文化部“五七”干校返京在国务院出版口报到,接触也逐渐多了起来。但“文革”那种特殊政治环境使这位出版界的智者和行家难有作为。他当年曾悄悄对我说,现在普遍存在两种人:一种是总想怎么整人,一种是总想怎么不被人整,这怎能使人做好工作呢?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位多年受到压抑的智者和行家像获得了新生一样,从精神状态到工作业绩都达到了成熟出版家的高峰期,抓改革、促发展、著书立说,稳步前行。我也在同他的接触中深受教益。我曾这样说过:“我从他对出版事业的贡献中得益,使我有一种‘坐享其成’之感;我从他思想品格中得益,却使我感到同他有一种难以缩短的差距。”
王益同志一生忠诚于出版事业,为出版事业一直在不倦地追求,不倦地奋斗。在职时是这样,离休后还是这样。他对我国出版的历史和现状有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对外国出版业做过比较系统和深入的考察,写了大量立意新颖、论据严谨、文风朴实的文章,他对中外出版比较研究的成果对我国出版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对出版实践问题的解决,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著有《王益出版发行文集》、《王益印刷文集》、《王益印刷发行文集》续编和三编、《出版工作基本知识》等;主编《图书商品学》,亲自撰写《前言》和有较高理论水平的《总论》(上编)第一至第八章。他在80高龄时,还翻译出版了美国一位出版家的专著《图书出版的艺术与科学》,赠送给出席庆祝他从事出版工作60周年座谈会的同志,使与会者不仅能够读到这部有借鉴意义的专著,而且更可以从中体验到这位老出版家对出版事业极其负责、精益求精和不断进取的精神。王益同志以他的出版学著作,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
以我几十年的接触,我认为王益同志最大的特点也是特长,是他的严谨求实的精神。他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从不夸夸其谈,也少有豪言壮语,总在勤勤恳恳、扎扎实实地工作着。大到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探求,如国家印刷技术改造专项的建议与筹划,小到一个技术性问题的解决,都要通过对大量的信息资料和准确数据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结论。工作中讲科学、严谨与准确,他首先做到了,也对他的追随者从严要求。1981年我起草国家出版局党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在讲出版重要地位时,不经意地写出:“有史以来,在整个人类文化绵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图书出版一直是传播和积累优秀文化的主要工具。”王益同志批道:“不能说‘有史以来’。中国是有出版事业最早的国家,历史也不过一千几百年。”对我未多加思考写下的这个“有史以来”,他只作批注而未作删改,这一细节多少也反映了他处世待人的一种风格。
王益同志不断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深受与他共事的人们及其继任者所称道。他不满足于现状,总是想多作贡献。他不守旧,一直在追求创新。20世纪80年代,王益同志已是出版战线的一位老兵了,而这位老兵却在书写新传,在不断创新历史。当年为打破独家垄断、搞活流通而推行发行体制改革的时候,是在这位老兵带领下,克服传统思想的束缚和习惯势力的阻挠,而不断取得改革的新成果,创出一片新天地的。读读这位老兵当年那些讨论发行改革的文章吧,你会感受到一位有个性的稳健的改革者在向你走来。当前,出版界正按中央的部署进行出版社的转企改制,然而,人们也许未曾注意,首先提出出版社应确定为企业而不应是事业单位的乃是王益同志,是他在《出版发行研究》1999年第一期发表的《事业乎?企业乎?》一文中提出的,进而引起出版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起到了当年引领出版舆论的积极作用。
我深情地思念着王益同志。王益同志对出版事业的重要贡献和不倦追求的思想品格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2009年3月1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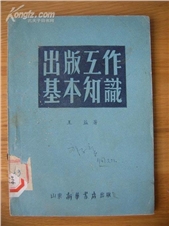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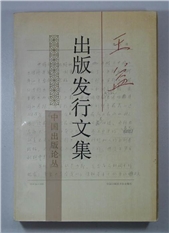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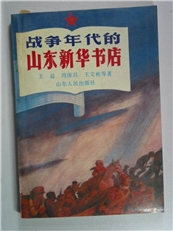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